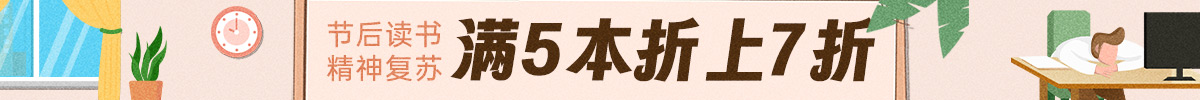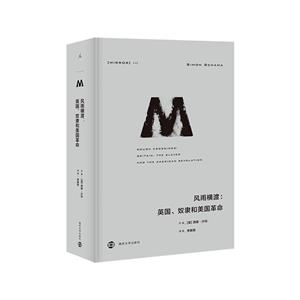-
>
西洋鏡第三十三輯 :中華考古圖志
-
>
(花口本)(精)讀一頁就上癮的唐朝史(全4冊)
-
>
長安夢華錄
-
>
安史之亂
-
>
埃及法老圖坦卡蒙
-
>
紙上起風雷:中國文人(1900—1949)
-
>
西洋鏡:第二十三輯 五脊六獸
理想國譯叢046:風雨橫渡:英國、奴隸和美國革命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5239595
- 條形碼:9787305239595 ; 978-7-305-23959-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理想國譯叢046:風雨橫渡:英國、奴隸和美國革命 本書特色
【圖書版次以實際收到為準】★ 美國和英國,誰主張的才是真正的自由與平等精神?在獨立戰爭中,北美革命者憑借人人生而平等的口號樹起自由平等的大旗;但是,另一邊的英國絕非什么邪惡勢力,它也在致力于另一項代表自由平等的事業:解放黑人奴隸。因此,這場戰爭不僅是兩個民族間的戰爭,更是兩種精神間的戰爭。★ 革命者或奴隸主,哪個是北美愛國者的本來面目?大陸會議刪去杰斐遜在《獨立宣言》初稿中對奴隸制的控訴,簽署《宣言》的愛德華拉特利奇激烈反對黑人以參軍換取解放,就連華盛頓也百般阻撓戰敗的英國人設法幫助已重獲自由的黑人離開北美革命者宣揚所有人都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卻不愿意給予黑人這樣的權利。★ 大人物和小角色,誰是推動歷史車輪的決定性力量?美國是由一批被譽為國父的大人物建立的,但廢奴歷史的主角卻是一群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他們是負責整理倉庫的軍需官格蘭維爾夏普、給人看病講道的醫生牧師詹姆斯拉姆齊、到處托關系找工作的海軍上尉約翰克拉克森,以及*重要的無數有名無姓、掙脫奴役枷鎖的黑人:喬、大衛、比利、約翰、彼得、湯姆、曼努爾★ 理想或現實,哪個是人類歷史畫卷的底色?獨立戰爭之初,部分革命者曾提出廢除奴隸制,但為了團結南方奴隸主勢力,*終被迫放棄了主張;戰爭結束后,英國廢奴者帶領黑人前往西非,夢想在那里開創一個黑人的自由王國,然而卻遭遇私人利益與經濟現實的阻撓,*終以建立塞拉利昂殖民地而告終。歷史往往是現實考量與妥協的結果,很少沿著理想的軌跡筆直前進。
理想國譯叢046:風雨橫渡:英國、奴隸和美國革命 內容簡介
1772年初夏的一個早晨,倫敦城內外幾乎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威斯敏斯特廳,靜靜等待王座法院大法官做出一個決定人類未來的判決:黑人奴隸是否應該獲得自由?判決的消息猶如一陣旋風刮過大洋,在北美十三個殖民地的無數黑人間點燃了一場希望之火。他們掙脫奴役的鎖鏈,從此奮身于追求自由的斗爭中。 在本書中,西蒙·沙瑪以激情澎湃、超群絕倫的敘事藝術,講述了美國獨立戰爭前后,眾多不知名的廢奴主義者與黑人為解放奴隸而斗爭的故事。他們認為,自由是屬于全人類的權利,不因膚色有別。廢奴者們在法庭上為遭人綁架的黑人慷慨陳詞,帶領他們穿越槍林彈雨的北美戰場,橫渡風暴肆虐的大西洋,*終重返非洲故鄉,在野蠻荒蕪的塞拉利昂開創新的國度。蓄奴者的阻撓、革命者的虛偽、英國政府的干擾,甚至黑人同胞見利忘義的背叛行徑,種種艱難險阻,都無法泯滅他們追求和捍衛自由的決心與勇氣。
理想國譯叢046:風雨橫渡:英國、奴隸和美國革命 目錄
圖片列表
主要人物
“英國·自由”的希望
**部分 格里尼
**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二部分 約翰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結束,開始
大事年表
注釋與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致謝
索引
理想國譯叢046:風雨橫渡:英國、奴隸和美國革命 節選
“英國·自由”的希望 喬治三世(George III)的軍隊在約克鎮(York)向華盛頓將軍投降十年之后,英國·自由(British Freedom)還在北美堅持著。同西庇阿·耶曼(Scipio Yearman)、菲比·巴雷特(Phoebe Barrett)、耶利米·皮吉(Jeremiah Piggie)、斯瑪特·費勒(Smart Feller)等在內的幾百人一樣,他正在普雷斯頓(Preston)——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東北幾英里處的一個小鎮——附近的貧瘠土地上討生活。 就像普雷斯頓的大部分人那樣,英國·自由也是黑人,出生在某個較為溫暖的地方。可現在,他成了一介貧民,困在藍云杉林和大海之間那個飛沙走石的角落里。不過,英國·自由要比大部分人都幸運。因為他的名下有四十英畝地,以及一英畝半被哈利法克斯的律師助理欣然稱作“城鎮地皮”的土地。那里看起來不像是個鎮子,只是一片空地中間立著幾間簡陋的小屋,幾只雞趾高氣昂地轉來轉去,偶爾還有一兩只渾身是泥的閹豬。有些人設法搞來了幾頭牛,把地上光禿禿的灰石頭清理干凈,種上了一片片的豆子、玉米和卷心菜,然后同建筑木材一起拉到哈利法克斯的市場上去賣。但就算那些日子過得紅紅火火的人——以普雷斯頓的標準來衡量——也經常得跑到野外打兩只環羽松雞,或者去村子南邊的咸水湖上碰運氣。 他們在那里干什么?不光是活命。英國·自由和其他村民在堅守的,除了新斯科舍的一隅,還有一份承諾。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還把承諾打印出來,讓英國軍官代表國王本人簽了字,說持有者某某某可自由去他或她想去的任何地方,從事他或她選擇的任何職業。這對曾經為奴的人來說意義重大。而國王金口玉言,當然不可能反悔。“黑人先鋒連”及其他人用他們在美國戰爭末期的忠誠服務,換來了兩份價值難以想象的恩賜:自由和土地。他們告訴自己,這是他們應得的。他們干的是*險、*臟、*累的活兒:在美國人中間當過間諜;在佐治亞(Georgia)的沼澤里當過向導;在危險的沙洲里當過船只領航員;在查爾斯頓的護城墻上當過工兵,身邊不斷有人被法國的加農炮炸得缺胳膊少腿。他們挖過戰壕;埋葬過渾身是痘的尸體;給軍官們的假發撲過粉;還曾敲著軍鼓機智地行軍,帶領兵團在災難中進進出出。女人則煮過飯、洗過衣、照顧過病號,給士兵身上的傷口涂過藥,還要努力保護子女們不受傷害,其中一些還打過仗,當過南卡羅來納的黑人騎兵和哈得孫河上的國王死忠水兵團伙,還做過黑人游擊隊員,襲擊新澤西的愛國者農場,能搶什么搶什么,蒙主保佑的時候,甚至還俘虜過一些美國白人。 所以,他們有功。所以,他們被賦予了自由,其中一些還得到了土地。但因為土壤貧瘠、亂石遍地,大多數人黑人都沒辦法自己清理、耕種這樣的土地,所以他們和他們的家人只得受雇于白人保皇黨。而這就意味著煮更多飯,洗更多衣,在餐桌旁伺候更多人,給更多的粉嫩下巴刮胡子,為了修路造橋而鑿更多石頭。可他們還是負債累累,有些人痛苦得無以復加,止不住抱怨他們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另一種奴隸制,就差名稱不同。 但名稱還是有意義的。英國·自由的名字就表達了很重要的東西:他已經不再是供人買賣的財產。盡管荒涼、艱苦,但普雷斯頓不是佐治亞的種植園。其他普雷斯頓人——德西莫斯·墨菲(Decimus Murphy)、凱撒·史密斯(Caesar Smith)——獲得自由后,顯然還保留了自己的奴隸名。但英國·自由出生或者被買來時肯定叫別的名字。在1783年,共有三萬名保皇黨(黑人白人都有)分八十一批坐船從紐約去了新斯科舍,而他可能就在某一次航行中,把原來的名字像腳鐐一樣甩掉了,因為在《黑人名冊》(Book of Negroes)中——里面記錄著所有男女自由人的名字,他們可以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沒有人叫英國·自由這個名字。毫無疑問,有些人改了名字,以反映自己的新身份:如詹姆斯·拉戈里(James Lagree),他曾經是查爾斯頓的托馬斯·拉戈里的私人財產,去了新斯科舍后,把名字改成了解放·拉戈里(Liberty Lagree)。當然,英國·自由也有可能是在早期的某次保皇黨大轉移中——1776年從波士頓(Boston)或者1782年從查爾斯頓——去了新斯科舍。在戰爭結束和英國艦隊離開之間那可怕的幾個月里,美國的種植園主曾努力搜尋逃跑奴隸的下落,所以他們中的很多人為了避免被發現而改換了姓名。英國·自由可能更進一步,給自己取了一個同時還可以表達愛國自豪感的假名。但無論他走的是哪條路線,無論他此刻在承受什么樣的磨難,英國·自由給自己選的名字,都宣揚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信念:將非洲人從奴隸制中解放出來的,更有可能是君主立憲制的英國,而非美國這個新生的共和制國家。盡管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在《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曾把美國的奴隸制歸咎于“基督教國王”喬治三世,但英國·自由這樣的黑人對國王卻不是那么看的。恰恰相反,國王是敵人的敵人,所以是他們的朋友、解放者和捍衛者。 視英國國王為恩人的傳統由來已久。比如1730年在新澤西的拉里頓縣(Raritan County),一場奴隸起義的計劃被發現后,一名黑人告發者對一個叫雷諾茲(Reynolds)醫生的人說,起義原因是“一群惡棍”違抗“喬治國王讓紐約總督解放他們的積極命令”。 三十多年之后,那些被公然排除在美國自由的庇佑之外的黑人曾嘲諷“他們在這個國家所謂的那種自由”(塔沃斯·貝爾[Towers Bell]語)。在戰爭結束時,貝爾以“真正的英國人”署名寫信給英國軍隊的領導,說他從英國被強擄到巴爾的摩(Baltimore)“賣為奴隸,在這個造反的國家遭受了四年*可怕的野蠻行為”。現在戰爭結束了,他別無所求,只想回到“親愛的故鄉英國”。 成千上萬的非洲裔美國人,盡管很清楚英國人在奴隸制的問題上遠非圣人,但依然堅持非理性地相信英國式自由。到英國法庭在1800年明確裁定奴隸制不合法之前,新斯科舍一直有奴隸和自由黑人,英屬加勒比地區更是有成千上萬。但即便如此,1829年,早期激進的廢奴主義者之一、非洲裔美國人大衛·沃克爾(David Walker)還是在波士頓發表了他的《告世界有色公民書》(“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宣稱“英國人”是“有色人種在地球上*好的朋友。雖然他們曾經多少壓迫過我們,而且現在在西印度群島(West Indies)上建立了殖民地,嚴重壓迫著我們——但撇開這些不說,他們(英國人)為改善我們的狀況所付出的努力,是地球上所有其他國家加起來的一百倍”。相比之下,那些美國白人故作虔誠信教之態,偽善地呼喊著空洞的自由口號,所以被他冠以*卑鄙的虛偽惡名。而英國國會廢除奴隸制的法令在1834年正式生效,以及英國皇家海軍一直在非洲西海岸追剿販奴船只,更有利于這種英國人待非洲人很仁慈的慷慨評價。1845—1847年間,黑人演說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到英國進行巡回演講,批判美國奴隸制度的邪惡時,便附和了沃克爾的恭維,將“英國人”視作解放者。后來的1852年,他又在獨立紀念日的演講中自問道:“7月4日國慶日對奴隸有何意義?”然后自答曰:“你們崇高無比的獨立,僅僅揭示了我們之間無法估量的距離……你們可以歡慶,但我必須哀悼。” 英國是否有資格稱得上在所有民族和帝國中擁有*開明的種族觀念?實話實說,這個問題有待商榷。比如在1861—1865年的南北戰爭期間,英國的政策和英國人就更傾向于支持蓄奴的南方邦聯,而非北方的聯邦政府,原因則主要是為了遏制共和國氣勢洶洶的擴張。但毫無疑問的一點是,在革命戰爭期間,確實有成千上萬被美國南方奴役的非洲人將英國視為他們的拯救者,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險奔赴皇家軍隊的前線。因此,要還這個驚人史實一個公道,就必須從全新而復雜的角度,來講述英美兩國在革命期間和之后的沖突歷史。 誠然,有很多黑人聽說或讀到愛國者的戰爭是一場解放戰爭后,雖然心中有所懷疑,但還是愿意相信他們。因此,如果說那邊有一個英國·自由,那么這邊就會有一個迪克·自由(Dick Freedom)——和一個杰弗里·解放(Jeffery Liberty)——在康涅狄格(Connecticut)的兵團為美國打仗。黑人曾在康科德(Concord)、邦克山(Bunker Hill)、羅德島(Rhode Island)以及*后的約克鎮為美國的革命事業奮戰捐軀(在約克鎮戰役中,他們還被安排到了*前線,但這到底是贊揚他們的勇氣,還是把他們當成了無足輕重的犧牲品,我們不得而知)。在新澤西發生的蒙茅斯戰役中,交戰雙方的黑人軍隊相互殘殺。但其實,直到英國開始在1775年和1776年聲勢浩大地征募黑奴之前,各殖民地(包括北方那些殖民地)的議會,以及它們組成的大陸會議,都不愿意讓黑人參軍。比如新罕布什爾(New Hampshire)便很有代表性,禁止瘋子、傻子和黑人參加該州的民兵組織。1775年秋天,那些已經在愛國者民兵組織服役的黑人被勒令退伍。在劍橋(Cambridge)的營地,喬治·華盛頓雖然聽到了其他軍官和平民代表的強烈反對,但卻不愿意放走那些黑人志愿兵,于是他把這個問題交給了大陸會議來決定。不出所料,在大會上,愛德華·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等南方代表對于武裝黑人奴隸的強烈恐懼,蓋過了對黑人服役的冷淡感謝。就連武裝的自由黑人也是個麻煩。我們敢相信他們不會把造反的種子播撒到那些黑人奴隸中間嗎?1776年2月,會議指示華盛頓,現有的自由黑人可以留下,但不要再征募新人了。當然,該會議創建的大陸軍則完全禁止黑人奴隸參加。 相反,1775年11月7日,弗吉尼亞*后一任英國總督、鄧莫爾伯爵約翰·默里卻在皇家海軍“威廉號”上發表宣言,斬釘截鐵地承諾,所有逃離叛軍種植園的奴隸到達英國前線,并在軍中擔任一定職務后,都可以徹底獲得自由。這個承諾更多是出于軍事考慮,而非人道主義動機,有一個能活著看到諾言兌現的英國·自由,就有更多的人會遭到無恥的背叛。不過,這種機會主義策略也帶來了一些好處。鄧莫爾伯爵的承諾得到了英國政府的認可和豪將軍(General Howe)、克林頓將軍的重申(他們擴大了有權獲得自由之人的定義,將黑人女性和兒童也包括進來),傳遍了奴隸世界,很快,成千上萬的黑人便行動起來。在黑人奴隸的眼中,美國獨立戰爭的意義完全被顛覆了。從1775年春天到1776年夏末,那場被吹噓成解放的戰爭,在佐治亞、南北卡羅來納和弗吉尼亞的很多地方,成了一場為延續奴役制度而打的戰爭。這之中的邏輯歪曲到了有悖常理的程度,但人們又對之習以為常,連喬治·華盛頓都將承諾解放奴隸和契約勞工的鄧莫爾伯爵說成是“人權的頭號叛徒”,而那些致力于維持這種奴役狀態的人卻是為自由而戰的豪杰。 對于黑人而言,“英國人要來了”這條消息給了他們一個希望、慶祝和行動的理由。比如,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的一位路德派牧師亨利·梅爾基奧爾·米倫伯格(Henry Melchior Muhlenberg)就很清楚這一點,他曾寫道,黑人“心中暗自希望英國軍隊會打勝仗,因為那樣的話,所有黑奴都將獲得自由。據說,這種情緒普遍存在于美國的所有黑奴中”。偶爾,真話也會從愛國者的詭辯護甲中戳出來。比如1775年12月,隆德·華盛頓(Lund Washington)在給遠房堂兄喬治寫信時就曾說,黑人和契約勞工正在飛速逃離華盛頓家的莊園,“要是他們覺得自己有機會逃跑,就沒有一個會不愿意離開我們……自由的滋味太甜了”。 各位國父對于自家奴隸的失蹤情況直言不諱,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中有很多人都遭受了嚴重的個人損失。比如,托馬斯·杰斐遜雖然曾試圖在《獨立宣言》中加入一段抨擊奴隸制的內容(被大陸會議刪去了),但在1781年春季的幾個星期中,他也損失了三十名家奴,當時康沃利斯侯爵的部隊離杰斐遜的莊園蒙蒂塞洛(Monticello)不遠。杰斐遜認為,至少有三萬奴隸逃離了弗吉尼亞的種植園,企圖前往英軍前線——這一數字與本杰明·夸爾斯(Benjamin Quarles)、加里·納什(Gary Nash)、西爾維亞·弗雷(Sylvia Frey)、艾倫·吉布森·威爾遜(Ellen Gibson Wilson)、詹姆斯·沃克爾(James Walker)等大部分近代歷史學家的判斷相符。南方其他地區的情況如出一轍。早在1858年時,歷史學家大衛·拉姆齊(David Ramsay)就估算,南卡羅來納三分之二的奴隸都逃跑了;而且其中有很多向英方投誠,雖然肯定不是全部。總的算下來,獨立戰爭期間逃離種植園的奴隸約有八萬到十萬人。愛國領袖們越是義正詞嚴地譴責萬惡的漢諾威(Hanover)暴君對北美的奴役,他們自己的奴隸便越是用腳投票。比如,拉爾夫·亨利(Ralph Henry)就把主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那裝腔作勢的宣言“不自由,毋寧死”牢牢記在了心上,只不過與其作者的原本意圖有所差別:一有機會,他便逃往了英軍前線。(諷刺的是,這句話后來被19世紀的黑人廢奴主義者和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m X]等20世紀的黑人解放者當作里了他們的戰斗口號!)其他簽署過那份斷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文件且損失了奴隸的人,還包括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和本杰明·哈里森五世(Benjamin Harrison,第九任總統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的父親),后者損失了二十名奴隸,其中包括安娜·奇斯(Anna Cheese)和龐培·奇斯(Pompey Cheese)夫婦,這兩人一路逃到紐約、新斯科舍和塞拉利昂,以及來自南卡羅來納的簽署人阿瑟·米德爾頓(Arthur Middleton)損失了五十名奴隸。后來成為州長的約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的奴隸龐培(Pompey Rutledge)和弗洛拉(Flora Rutledge)投靠了英國人,《獨立宣言》*年輕的簽署者、激烈反對黑人參軍的愛德華·拉特利奇也損失了奴隸。來自南卡羅來納、綽號為“沼澤狐貍”的弗朗西斯·馬里恩將軍(General Francis Marion)——他的種植園黑奴曾在梅爾·吉布森(Mel Gibson)的電影幻想《愛國者》(The Patriot)中被刻畫成了熱切地追隨主人、為爭取自由而戰的人——也至少有一名奴隸投靠了英軍:這個叫亞伯拉罕·馬利安(Abraham Marrian)的人很可能加入了1782年夏天被動員起來的一支小型黑人騎兵連,在南卡羅來納的瓦德布種植園攻打過馬里恩(這樣更能說得通),而非同他并肩作戰。此外,不得不提的還有,1776年初,當喬治·華盛頓駐扎在劍橋公地絞盡腦汁地掂量征募黑人入伍的利弊時,他自己的奴隸、出生在西非的亨利·華盛頓也逃到了英軍的大后方。和其他黑人保皇黨一起在新斯科舍的伯奇鎮流亡的亨利·華盛頓會動人地說自己是一個“農民”,但為他的四十英畝土地和自由提供保護的其實是英國國旗。 這段大規模逃跑的歷史固然令人震驚,曾被加里·納什貼切地描述為獨立戰爭中的“骯臟小秘密”,但它又是那種*佳意義上的震驚,迫使人們對那場戰爭進行了一場姍姍來遲的誠懇反思,那就是美國獨立戰爭從根本上而言其實還牽涉了第三方。而且這個由非洲裔美國人組成的第三方占到了殖民地二百五十萬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具體到弗吉尼亞的話,更是占到了百分之四十。當然,在對待卷入那場斗爭中的黑人時,無論是英方還是美方,表現都不怎么好。但到*后,英國·自由以及和他一樣的很多人意識到(即便當時他們已經是自由黑人了),皇家的路似乎能為他們提供更可靠的解放機會,共和國的路不行。黑人的孤注一擲與英國的父愛主義糾葛在一起后呈現出的這段歷史,雖然結果往往充滿了慘痛的悲劇色彩,但仍然是非洲裔美國人爭取自由的歷史中一個影響深遠的時刻。比如,它催生了被認可為**位非洲裔美國人政治領袖的托馬斯·彼得斯中士。 彼得斯曾是尼日利亞埃貝族(Egbe)的王子,被法國的奴隸販子俘虜后賣到了路易斯安那(Louisiana),曾因屢次試圖逃跑而遭受鞭笞和烙刑,接著,被賣給北卡羅來納威爾明頓(Wilmington)的一位種植園主后,他*終逃到了英國人那邊。在喬治·馬丁上校(Captain George Martin)的主持下,彼得斯宣誓加入先鋒連,在戰斗中兩次負傷,被提拔為中士。后來,他先是定居在新斯科舍的北岸,接著又去了新不倫瑞克(New Brunswick),并代表他的黑人同胞前往倫敦,向國王請愿。彼得斯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人民領袖:頑強、英勇,雖然大字不識,但有一連串白人曾被他的傲慢態度觸怒,間接證明他顯然能說會道。他明顯沒有被作為非洲裔美國英雄而為人敬仰(不過倒是有幾個令人尊敬的例外情況),他的名字在美國高中歷史課本中更是完全未被提及,這樣的丑聞只能有一個解釋:彼得斯不巧是為錯誤的一方而戰的。無獨有偶,波士頓那些選擇加入英國而非美國革命事業的黑人得到的也是這種待遇。1770年,英軍槍殺暴亂者,制造了波士頓大屠殺,遇害者之一的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被奉為陣亡英雄。但為英軍作證的黑人理發師牛頓·普林斯(Newton Prince)的故事卻毫不意外地鮮為人知。這樣的冒失行為惹惱了愛國者后,普林斯被施以“涂柏油、粘羽毛”的私刑,所以也難怪他會在1776年選擇投奔豪將軍,并隨英軍撤離。同樣,另一位理發師布萊克·倫敦(Black London),在1776年曾告訴戰后成立的保皇黨索賠委員會的委員,他加入愛國者的民兵組織是受雇主脅迫,后來一有機會便開了小差,跑到亨利·克林頓爵士的手下當了四年兵,后又在兩艘戰艦上服過役。 無論這對國父們及其革命的正統歷史來說有多尷尬,非洲裔美國人解放的起源都與他們在戰時及戰后同英國的關系密不可分。不獨自由黑人的政治誕生于那場戰爭的炮火中,他們的基督教集會的獨特形式也是如此。正是保皇黨的非洲人在新斯科舍的謝爾本鎮及附近創建了*早一批自由的浸禮宗和循道宗教會;也是在那里,**批白人在黑人牧師的主持下改宗,在那些紅色的河水中接受了魅力超凡的牧師大衛·喬治為他們施行的洗禮。**批專門為自由黑人的子女開辦的學校也是在保皇黨大批移居到新斯科舍后開設的,而給孩子們上課的老師,比如普雷斯頓的凱瑟琳·阿伯內西(Catherine Abernathy)、伯奇鎮的斯蒂芬·布拉克,同樣是黑人。在一千多名“新斯科舍人”橫跨大西洋,重返非洲(這次是以人的身份,而非財產)*終抵達塞拉利昂后,美國黑人有史以來**次(只是太過短暫)體驗了一定意義上的地方法治和自治。還有一個**次,則是曾為黑奴的西蒙·普魯弗(Simon Proof)當選警官后,對一名被判玩忽職守的白人水手執行了鞭刑。 但是,黑人保皇黨的歷史遠遠不只是一系列的“**次”。這段歷史也揭穿了一個謊言,證明了黑人并非像人們以為的那樣,只是美國或英國戰爭策略中被動、輕信的棋子。無論是選擇站在愛國者那邊還是保皇黨這邊,無論識文斷字與否,很多黑人都十分清楚自己在干什么,雖然他們根本不可能預料到自己的決定會造成多么嚴重的危險、不幸和欺騙。通常情況下,他們的決定取決于這樣一種判斷:且不論早晚,一個自由的美國是否會被迫信守《獨立宣言》中的原則,承認自由和平等是所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或者(尤其在南方),鑒于逃跑者遭到追捕,并被送到鉛礦或者硝石廠做苦工的慘狀,那些華麗動聽的承諾是否可能被無限期地推遲兌現。畢竟,佐治亞和南卡羅來納為鼓勵白人入伍而提供的激勵措施,還包括在戰爭結束后可獲得一名自由奴隸,這可不是什么好兆頭。
理想國譯叢046:風雨橫渡:英國、奴隸和美國革命 作者簡介
西蒙·沙瑪(Simon Schama),英國作家、歷史學家,曾先后任教于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及藝術史教授,在藝術史、荷蘭史和法國史方面尤有建樹。著有《愛國者和解放者》《風景與記憶》《倫勃朗的眼睛》《猶太人的故事》等,作品曾榮獲沃爾夫森獎、W. H. 史密斯文學獎和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沙瑪還在BBC電視系列紀錄片《英國史》《藝術的力量》《文明》中擔任撰稿人和主持。
- >
巴金-再思錄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我與地壇
- >
回憶愛瑪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