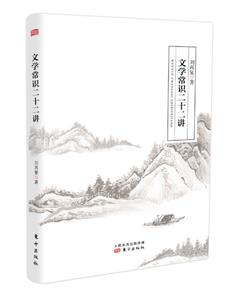-
>
野菊花
-
>
我的父親母親 - 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
>
吳宓日記續編.第7冊.1965-1966
-
>
吳宓日記續編.第4冊:1959-1960
-
>
吳宓日記續編.第3冊:1957-1958
-
>
吳宓日記續編.第2冊:1954-1956
-
>
吳宓日記續編.第1冊:1949-1953
文學常識二十二講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6083362
- 條形碼:9787506083362 ; 978-7-5060-8336-2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文學常識二十二講 本書特色
著名文學家、人文學者劉再復先生講述中西文學常識,涉及文學常識的方方面面,如文學的概念,文學的特性,文學的各項要素,文學的功能以及文學與自然、自我、宗教、道德、人生等之間的關系等,娓娓道來,在解讀文學的同時,更加注重心靈的養育。
文學常識二十二講 內容簡介
文學是多種精神價值創造形態中*自由的形態,是自由心靈的審美存在形式。
“文學的心靈”,一定是超功利、大慈悲、合天地的心靈。凡是不能切入心靈的作品,都不是一流的作品。
文學對于人生的意義恰恰在于它可以讓讀者超越人生的平淡狀態而進入詩意狀態。
通讀“文學常識課”,會發現它是極為完整的文學觀。無論是講述文學的本性、自性,還是講述文學批評與經典閱讀,或文學與其他范疇的互動與對話(如文學與自然、文學與文化、文學與政治、文學與自我等),知識之外,更訴諸良心與責任,澄明與節制。說到底,是先生對文學的至誠至愛。——潘淑陽
用心傾聽先生講述文學,就會發現文學是怎樣地保護著他,他又是怎樣地在文學中純化自己,用文學的元氣,守望著心靈的天籟。——潘淑陽
文學常識二十二講 目錄
文學常識二十二講 節選
一、何為心靈?
什么是心靈,這是一個大問題。正如“什么是文學”一樣,心靈也很難定義。
徐復觀先生曾說,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東方(中國)文化是“心”的文化。這也許可以說明東西方文化的側重點不同,但不能說西方文化就沒有“心”。其實,“上帝”就是一顆偉大心靈。這顆心靈光芒萬丈,照亮了兩千多年來無數人的道路。這顆心靈是西方愛的源泉,是精神本體。先不說“上帝”,就人文科學領域而言,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時期就開始探索“心靈”問題,尤其是探討心靈與靈魂的關系。亞里士多德還把心靈區分為“主動的心靈”和“被動的心靈”,“遭受的心靈”與“實現的心靈”。他假設被動的心靈會隨肉體而生滅,而主動的心靈則不朽不滅,帶有永恒性。借用亞里士多德的理念,可以說文學心靈指的正是主動的心靈,實現的心靈。它追求的是一種比肉體更長久的生命。
其實,各種宗教都是大心靈的體現,其教義都在塑造心靈。基督教呼喚的是“愛”的心靈,佛教呼喚的是“慈悲”的心靈。基督代表愛無量心,佛陀則代表慈無量心,悲無量心。愛與慈悲是矛盾的,愛往往無法慈悲。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中有一句話:“一個人愛的時候并不慈悲。”的確如此,一個極端的愛者,為了實現愛,往往很自私,很殘酷,排他性很強。不過,基督講的是“大愛”,與慈悲相同。 除了宗教,各種文化也總是要界定心靈,呼喚心靈。就中國文化而言,各家所界定的“心靈”內涵就很不同。儒家講“仁愛之心”,道家講“齊物之心”,墨家講“兼愛之心”。孟子講“四端”,即講人與動物(禽獸)的區別就在于人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他講“人禽之辨”,說人與動物的區別只有一點點(幾稀),人之所以成為人,只因為人有不忍之心。后來,明代思想家王陽明創造了“心學”,把“心”強調到絕對的程度。所謂“心學”,也就是“心本體”之學,說明的是心為萬物之源,萬物之本,不僅“心外無物”,而且“心外無天”。心不僅包容一切,而且決定一切。在王陽明之前,中國的禪宗,宣揚的其實也是心性本體論,慧能“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而是心動”的著名判斷,就是“心外無物”——心動決定物動的判斷。
我把文學定義為“自由心靈的審美存在形式”,把文學事業界定為心靈的事業,并確認心靈為文學的**要素,正是把心靈視為文學的本體(根本)。但是,對文學中的“心靈”,我們還須進一步界定。因為文學呈現的是人性,我們必須了解心靈在當中的位置,這個問題也許需要幾部學術專著才能說清。我們今天只能說,復雜紛繁的人性至少包括動物性、人性和神性,即人性可下墜為動物性,也可上升為神性,心靈則是人性與神性組合的精神存在,它可以駕馭并導引人性來拒絕動物性。如果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來描述,心靈不屬于本我。它不是本能,而是理性的“自我”與神性的“超我”結合的精神存在。也就是說,我們所講的心靈,既不是肉身意義的心臟,也不是超肉身的神靈,而是存在于我們身內又導引肉身提升的靈魂性存在。 文學常識課不是生命科學課,也不是“靈魂”宗教課,在此只能對“心靈”作大體描述。
二、作家應有什么樣的心靈?
我讀過王安憶的《小說家的十三堂課》,我和她的文學理念完全相通,她也把文學視為心靈世界。她在開篇就說:小說是什么?小說不是現實,它是個人的心靈世界,這個世界有著另一種規律、原則、起源和歸宿。但是筑造心靈世界的材料是我們所賴以生存的現實世界。小說的價值是開拓一個人類的神界。 王安憶講的是小說,如果把“小說”改為“文學”,那么,她說的正是文學真理。文學所創造的正是“個人的心靈世界”。她特別加上“個人”二字,這很重要。文學呈現的心靈是充分個人化的心靈世界,不是群體心靈的符號,也不是黨派心靈的符號。這個心靈世界有自己的原則。我常說“心靈原則”,也是指個人的心靈原則。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篇幅很短,卻成為百年來文學理論的經典,就因為它道破了文學的根本。他特別推崇李后主的詞,正因為李煜詞的心靈境界很高。王國維用一句話概說這種境界,說它具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的心靈境界。中國有三個帝王后來都曾為敵方俘虜而變成囚徒,人生發生了巨大的落差。落差之后,其心靈也奔向不同的方向。這三個帝王分別是越王勾踐、宋徽宗趙佶及南唐后主李煜。這三位帝王的心靈境界各異,勾踐想的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滿心想復仇;宋徽宗內心只有個人的哀戚;唯有李煜,推己及人,從個人的不幸出發而想到普天之下蒼生的不幸與苦難,把個體的悲哀化作普世的悲情,寫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動人詞句。在文學中,心靈很具體,王國維用“天眼”、“佛眼”將李后主與宋徽宗的心靈相比(未言及勾踐),給后人很大的啟迪,同時告訴我們:作家、詩人的心靈,不是一般的心靈,它應當像“天眼”、“佛眼”、“法眼”、“慧眼”一樣,具有“天心”、“佛心”、“法心”、“慧心”,或是《人間詞話》所說的“赤子之心”,即童心。詩人*值得驕傲的,是他胸中永遠跳動著一顆單純的童心。王國維曾概說“天才”的幾個特征,其中一個便是赤子之心。 關于作家的主體心靈,我有幸聽過高行健的直接表述。他說他一直懷抱三種心靈:“敬畏之心”、“謙卑之心”與“悲憫之心”。“敬畏之心”并不是簡單地對某某人的尊敬,而是承認在人類之外有一種不可知的力量存在。這種冥冥之中的力量不一定是上帝,它非常強大而神秘,人類永遠不可能認識它,只能感受它,所以自然而然會對它產生敬畏,比如我們對大自然、大宇宙便會有敬畏之心。康德晚年提出“物自體,不可知”,就是在他研究了一輩子哲學后,發現宇宙不可解釋只能敬畏。愛因斯坦*后皈依上帝,對如此偉大的理性主義者的皈依行為,我們或可作這樣的解釋:對于愛因斯坦來說,重要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人需不需要有所敬畏。俄國的思想家別爾嘉耶夫在《論人的使命》中認定以人的同等水平無法把人看清,只有用比人更高的水準(神性水準)來看人,才能把人看得清楚。作家的心靈就必須立足于比人類更高的水準之上。“謙卑之心”也不僅是指謙謙君子風度。現在在中國大陸,尼采的書一本接著一本出版,崇拜尼采的人仍然不少。但高行健對尼采一再批評,這點很難得。他提出應當正視人乃是“脆弱的人”,而非“大寫的人”或者“超人”,這種思想的緣起就是他的謙卑之心。第三個就是“悲憫之心”,這一點與莫言不約而同。
“悲憫之心”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尤其是大悲憫之心。關于這種心靈,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曾經鄭重地撰文闡釋過。這一闡釋,實際上道破了他在文學創作上獲得成功的密碼。該篇文章發表于前幾年的《當代作家評論》,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他獲獎后,上海文藝出版社再版他的長篇作品系列,他又以這篇文章作為“代序言”,題為:“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現在我把其中*重要的段落節錄出來: 大苦悶、大抱負、大精神、大感悟,都不必展開來說,我只想就“大悲憫”多說幾句。……悲憫不僅僅是“打你的左臉把右臉也讓你打”,悲憫也不僅僅是在苦難中保持善心和優雅姿態,悲憫不是見到血就暈過去或者是高喊著“我要暈過去了”,悲憫更不是要回避罪惡和骯臟。……站在高一點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壞人,都是可憐的人。小悲憫只同情好人,大悲憫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惡人。
……只描寫別人留給自己的傷痕,不描寫自己留給別人的傷痕,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揭示別人心中的惡,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惡,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有正視人類之惡,只有認識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才是真正的悲劇,才可能具有“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憫。 特別引用莫言關于“大悲憫”的思考,是因為這兩段話擊中了文學心靈的要害。大悲憫之心,正是作家主體的真心靈。而大悲憫包含著兩重*關鍵的意思,一是無論“好人與壞人”,都是可憐的人。悲憫只同情好人,而大悲憫則同情一切眾生,包括同情惡人。二是大悲憫不僅要正視他人的傷痕與丑惡,更要正視自己的傷痕與丑惡,悲憫他者,更要悲憫自我。只有同時正視人類和自我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以及這些弱點導致的悲慘命運,才是真正的悲劇。莫言這一見解,是當代世界文學中*為深刻的心靈解說。我們只要想想俄羅斯文學——兩座巔峰——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會明白莫言說的是什么。托爾斯泰*后的行為語言是離家出走,“逃離”的大行為語言所蘊含的正是大悲憫之心,是他承受不了人間的罪惡和自我的罪惡。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靈魂拷問,則是對一切人的拷問,好人,壞人,被敬重的人、被侮辱的人,也包括他自己。他為什么會拷問出犯人罪惡掩蓋下的“潔白”?這是因為他的大悲憫。他的創作整體為什么讓人感到那里是一個“復調的世界”(巴赫金語),一個可憐的世界?也是因為他的大悲憫。文學的*高境界(或稱宇宙境界或稱審美境界)高于道德境界,其原因就在這里。道德只講除惡揚善,但看不到所謂“壞人”在人性深處與好人的相通之處。只知說教的道德家僅審判別人卻不知自身的可憐、脆弱、渺小與卑劣,缺乏對自身黑暗的洞察與悲憫。我在上學時背誦唐詩,其中元稹的名句一直刻在心里,那就是“閑坐悲君亦自悲”。這首詩是寫給妻子的悼亡詩。但我們可以把詩意加以引申,把“悲詩”擴展為悲憫甚至大悲憫——大悲憫包括“悲君”,也包括“自悲”,即正視自己的弱小、渺小,對*愛者的死亡一籌莫展,只能“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
文學常識二十二講 相關資料
文學是多種精神價值創造形態中最自由的形態,是自由心靈的審美存在形式。
“文學的心靈”,一定是超功利、大慈悲、合天地的心靈。凡是不能切入心靈的作品,都不是一流的作品。
文學對于人生的意義恰恰在于它可以讓讀者超越人生的平淡狀態而進入詩意狀態。
通讀“文學常識課”,會發現它是極為完整的文學觀。無論是講述文學的本性、自性,還是講述文學批評與經典閱讀,或文學與其他范疇的互動與對話(如文學與自然、文學與文化、文學與政治、文學與自我等),知識之外,更訴諸良心與責任,澄明與節制。說到底,是先生對文學的至誠至愛。——潘淑陽
用心傾聽先生講述文學,就會發現文學是怎樣地保護著他,他又是怎樣地在文學中純化自己,用文學的元氣,守望著心靈的天籟。——潘淑陽
文學常識二十二講 作者簡介
劉再復,著名文學家和人文學者。1941年農歷九月初七出生于福建南安縣。1963年畢業于廈門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曾任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所長,《文學評論》主編。80年代以《性格組合論》和《論文學主體性》等著作引發全國性討論。1989年夏天移居美國,先后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科羅拉多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加拿大卑詩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臺灣中央大學、東海大學等高等院校分別擔任過訪問學者、客座教授、講座教授、榮譽教授等,現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客座教授和高等研究院的客席高級研究員。
劉再復一手從事文學研究,一手從事散文與散文詩創作。其著作有《魯迅與自然科學》、《魯迅美學思想論稿》、《魯迅傳》、《性格組合論》、《文學的反思》、《論中國文學》、《放逐諸神》、《告別革命》(與李澤厚合著)、《共鑒五四》、《思想者十八題》、《傳統與中國人》、《罪與文學》(與林崗合著)、《現代文學諸子論》、《紅樓四書》、《雙典批判》、《高行健論》、《李澤厚美學概論》、《教育論語》、《什么是文學》以及《讀滄海》、《太陽土地人》、《人間慈母愛》、《漂流手記》、《遠游歲月》、《西尋故鄉》、《獨語天涯》、《共悟人間》、《滄桑百感》、《漫步高原》、《大觀心得》、《人論二十五種》等散文集。最近,北京三聯還出版了《劉再復散文精編》十卷及《賈寶玉論》等。在美國出版的英文譯著有《紅樓夢悟》、《雙典批判》;在韓國出版的韓文譯作有《共悟人間》、《人性諸相》、《雙典批判》、《面壁沉思錄》、《傳統與中國人》、《告別革命》等。其論文、散文還被譯為法、瑞、日、德等多種文字。
- >
自卑與超越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史學評論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旅程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