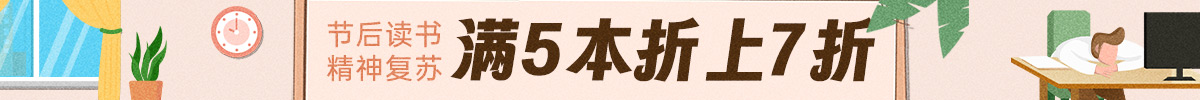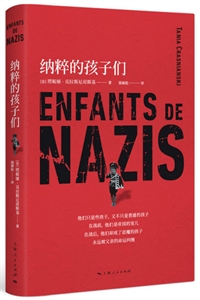-
>
西洋鏡第三十三輯 :中華考古圖志
-
>
(花口本)(精)讀一頁就上癮的唐朝史(全4冊)
-
>
長安夢華錄
-
>
安史之亂
-
>
埃及法老圖坦卡蒙
-
>
紙上起風雷:中國文人(1900—1949)
-
>
西洋鏡:第二十三輯 五脊六獸
納粹的孩子們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53424
- 條形碼:9787208153424 ; 978-7-208-15342-4
- 裝幀:精裝本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納粹的孩子們 本書特色
塔妮婭·克拉斯尼昂斯基著的《納粹的孩子們(精)》是一部反思二戰(zhàn)的歷史非虛構類作品,聚焦八個納粹高官的后代在戰(zhàn)爭前后的命運。作者克拉斯尼昂斯基深入探究了眾多現(xiàn)存檔案資料,仔細研讀了與納粹領導階層及其后代有關的司法文件、信函、書籍、文章、訪談內(nèi)容,從中整理出八個納粹孩子的圖像。全書涉及納粹頭目家庭生活、二戰(zhàn)及德國史進程、戰(zhàn)犯處理、戰(zhàn)后特殊人群的成長以及醫(yī)治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等主題,發(fā)人深省。 歌德倫·希姆萊、艾妲-戈林……這些第三帝國高官的子女們的命運如何?塔妮婭·克拉斯尼昂斯基追溯了他們的命運。——法國《星期日報》 塔妮婭·克拉斯尼昂斯基并沒有對這些第三帝國高官的子女們的行為做出個人評判。她記錄了他們每個人的態(tài)度——明白該如何面對一段遠超出自己命運的殘酷歷史。———一法國《觀點》
納粹的孩子們 內(nèi)容簡介
1940年,這群德國孩子只有4歲、5歲、10歲。他們在戰(zhàn)爭中備受優(yōu)待,因為他們擁有身居高位的父親。這些孩子分別是納粹要員希姆萊、戈林、赫斯、法郎克、鮑曼、霍斯、施佩爾、門格勒的子女。
對這些孩子來說,德國的戰(zhàn)敗是一場風暴,是與家人的分離,是優(yōu)越生活的終結,也是親身感受希特勒主義的恐怖。當時的他們天真無辜,對父親的所作所為一無所知。后來,他們逐漸了解了那些可怕的事實。成年后,他們中有些人譴責父輩的罪行并深感愧疚,有些卻無條件地懷念自己被全人類唾棄的戰(zhàn)犯父親。
本書回溯了這些孩子的經(jīng)歷,記錄了他們年幼時的家庭生活與成年后的人生。1945年以前,他們是英雄的子女,之后陡然淪為劊子手的后代。他們與父親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父輩的錯誤如何影響著后代的人生?……
納粹的孩子們納粹的孩子們 前言
引言
歌德倫、艾妲、馬丁、尼克拉斯,還有其他那些孩子們……
他們是希姆萊、戈林、赫斯、法郎克、鮑曼、霍斯、施佩爾、門格勒的小孩。這些孩子活在沉默中,他們的父親是罪犯,必須為當代歷史中*黑暗的年代負責。
可是歷史并不等同于他們的故事。
他們的父親罪大惡極,徹底泯滅天良。在紐倫堡大審判中,面對相關指控,他們的父親異口同聲,毫不猶豫地申辯無罪。但歷史是否記得,這些人也是為人父者?大戰(zhàn)結束后,在一種消除罪惡感的集體欲望中,某些人主張人民無辜,設法將納粹德國的殘暴及種族滅絕行徑完全歸咎于第三帝國的主要領導人物。至于那些受審的要人及其他許多納粹分子,為了逃脫罪責,他們會強調(diào):“那一切都是因為希特勒……”
那么,這本書里談到的孩子們,他們又有什么樣的人生歷程?他們繼承了一個共同的包袱:他們的父母消滅了數(shù)以百萬計的無辜人民。他們的名字被永遠蓋上可恥的烙印。
人是否應該覺得自己必須為父母所犯的罪行負責,甚至因此感到愧疚?家庭背景在我們的年少歲月中無法挽回地形塑了我們。盡管社會上的普遍認知是父母犯的錯不該由子女背負責任,但當一個人傳承到那么可怕的包袱,他不可能不受影響。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為人父者有兩條命,自己的命和兒子的命”,“龍生龍,鳳生鳳……”那些納粹要人的孩子們后來成了什么?他們怎么承受那么陰森恐怖的家庭遺產(chǎn)?
一名不知悔改的納粹曾經(jīng)對訪問他的猶太裔以色列外孫女說:“覺得自己有罪的人,就是有罪的人!”然后他泰然自若地給了她忠告:“跟那一切保持距離,這樣人生會簡單許多。”
要這些孩子們評斷他們的父母是非常困難的事。對于生育我們、撫養(yǎng)我們的父母,我們?nèi)狈陀^評斷所需的距離。情感聯(lián)結越是密切,道德判斷就越不容易。無條件認同,或者全面排斥?當家庭的過往如此駭人,我們?nèi)绾巫蕴帲窟@些納粹要人的兒女們有各自的立場,有些徹底反對父母,有些則與父母口徑一致,但很少有人采取中立態(tài)度。有些人一方面堅決摒棄父輩的作為,一方面卻能找到辦法繼續(xù)愛他們的父親。有些人永遠不可能愛一個“怪獸”,因此他們在內(nèi)心全盤否認那個黑暗面,借此維持一種無條件的孝心。另外還有一些人陷入對父親的排斥和仇恨。他們繼承到的過去宛如沉重的腳鐐,他們必須在日常生活中承受它,不可能對它視而不見。有人決定承認一切,有人走上心靈宗教的道路,甚至有人為免“遺傳罪惡”,決定結扎,或者透過自瀆的方式贖罪。否認、壓抑、認同、愧疚,所有人都得設法找到能讓他們面對過去的途徑,無論他們是否清楚意識到自己在做這件事。
這些孩子們大部分(曾經(jīng))生活在德國。其中有些皈依宗教,甚至成為天主教神甫或猶太教拉比。這么做是不是為了驅邪,借此解除身為罪犯之子的命運魔咒?舉阿倫•希爾-雅許夫(Ahron Shear-Yashuv)的例子,雖然他的父親并不是納粹政權的高官或重要執(zhí)行者,但他還是決定成為以色列軍的拉比。阿倫的本名是沃爾夫岡•施密特(Wolfgang Schmidt),他在修讀神學期間決定不要當天主教神甫,因為他不贊同天主教教義。他強調(diào),猶太大屠殺只是促使他皈依猶太教的部分原因,并且表示“猶太教在某些方面的確有迥異于其他宗教的特殊性,但寬宏大量也是它的特質。確實,皈依者不只會受到接納,他甚至有機會擔任拉比,在以色列國防軍當隨軍神甫及指揮官”。本古里安大學心理學教授丹•巴爾-昂(Dan Bar-On)認為這種類型的皈依旨在加入“受害者社群,擺脫歸屬于罪犯社群的心理負擔”。這種做法是不是在逃避過去,而不是勇敢面對它?皈依者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會給出各種不同回答。不過,宗教的洗禮確實讓某些人得以克服個人背景的重擔。
戰(zhàn)后力求復興的德國設法借由緘默驅魔,處在那樣的氛圍中,納粹的后代必須對自己做許多心理建設,才能讓自己站起來。
我在我外公生前跟他很親,他曾在德國空軍當職業(yè)軍人,住在黑森林深處的一棟狩獵小屋。他一輩子都不愿跟我提他生命中的那個階段。而且不是只有他這么做。在許多年間,戰(zhàn)爭的沉默身影飄蕩在德國和法國上空。戰(zhàn)爭的夢魘至今揮之不去,但人們愿意開口說話了。我小時候,所有人都屈服于沉默的宰制。跟我的外祖父一樣,戰(zhàn)后的幾個世代人們一直避免談論這個議題。某些人后來甚至采取啞巴策略,對那個時代只字不提,因為他們害怕玷污父母在他們心中的形象。這些人是否真的想知道他們的父母是什么樣的人,以及他們在德國歷史上那個黑暗時期涉入得有多深?答案是不見得。記憶并未傳承。為了逃避那個過去,我的德國母親在二十歲時選擇獨自到法國生活。她一直想要成為法國人,而當我開始著手寫這本書時,她的反應是不解。為什么處理這樣的題材?為什么繼續(xù)談這件事?這些都是我們不常問的問題。
我有德國、法國、俄國這三重家世背景,其中德國這個部分對我的人格施加了獨特的影響。德國的歷史被強加在我的生命中。安娜•韋伯曾說:“那是不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負擔?它從*初就存在,而且不會消失;沒有一個俄國人能代表古拉格,沒有一個法國人能代表法國大革命或殖民主義,他們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民族歷史。”然而,德國和納粹卻被畫上等號。
我對社會邊緣人的興趣促使我研究監(jiān)獄,然后成為刑事律師。這個職業(yè)為我?guī)韺懽鞅緯璧膰乐敹取辽傥沂沁@么希望——讓我憑借它援引歷史事實,以及探討書中所提的納粹孩子們對那些事實的觀感。透過他們的案例,我設法理解我們的過去在這個我們不顧一切想要取得主體性的世界中代表著什么。
真相與現(xiàn)實有時是非常沉重的負擔。有人傾向尊重家庭的秘密,即使導致那些秘密形成的人并非他們的家人。此外,毫無疑問的是,那些納粹要員沒有勇氣和力量向孩子們吐露他們犯下的暴行。
納粹高官的小孩大部分都不希望變更姓氏,這可能正是因為那個家姓無論如何也撇不開。某些人——例如阿爾貝特•施佩爾或馬丁•鮑曼的兒子——甚至冠上跟父親一樣的名字。赫爾曼•戈林的侄孫馬蒂亞斯•戈林說他喜歡自己的姓氏,其他一些人則表示姓氏無關緊要,繼承到什么姓就是什么姓。艾希曼的兒子表示:“逃避這個姓氏無法使問題改變,人不可能逃脫他的過去。”還有另外一些人——例如歌德倫•希姆萊和艾妲•戈林——對自己的父姓感到驕傲,而且非常景仰他們的父親。
奧斯維辛集中營指揮官魯?shù)婪?#8226;霍斯曾經(jīng)宣稱:“即使我是在執(zhí)行滅絕措施,我一樣過著正常的家庭生活……對我而言,家庭是神圣的,我跟它之間的聯(lián)結無法分割。”我們要如何理解這種矛盾?精神分裂的概念代表兩種互相矛盾的潛在可能性共存于自我中,這個概念可以用來解釋那些執(zhí)行命令者何以能夠一方面過著正常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卻屠殺數(shù)百萬人民。這種怪物怎么有辦法在親吻自己的小孩以后,走出家門殺害或命令別人殺害無數(shù)男女老少,毫無人性可言?我們該如何描繪希姆萊這號人物,想象他抱著他的“小娃娃”親吻,然后前往指揮部簽署命令處決兒童,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
輿論期望我們在那些罪犯身上識別出特定疾病,用來解釋他們的殘酷行為。但研究這個主題的人從來無法成功找出那些執(zhí)行命令者有什么獨有的人格。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時,一名負責檢查他的精神科醫(yī)生指出,艾希曼對妻子、兒女、父母、兄弟姐妹及朋友的行為“不只是正常,而且絕對值得嘉許”。我們寧愿相信那些人是一群嗜血怪獸,因為他們的“正常性”顯得更加令人毛骨悚然。普里莫•萊維曾說:“怪獸確實存在,但他們的數(shù)量太少,因此不至于構成真正的危險,比較危險的反而是所謂的普通人。”
在漢娜•阿倫特受人爭議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作者闡述了“惡的平庸性”這個概念,并描繪出一個小公務員的圖像,他充滿干勁但平庸至極,不懂得思考,無法分辨善惡。阿倫特沒有為他辯解,只是用他的例子強調(diào)非人性的因子存在于所有人身上,我們都必須不斷地“思考”,絕不能舍棄理性,要永遠保持質疑精神,才不會陷入惡的平庸性中。
本書所述及的納粹孩子們原本只知道他們父親的人格中的一個面向,另外那個面向是在德國戰(zhàn)敗后才被帶進他們的視野。大戰(zhàn)期間,他們年紀還太小,無法理解甚至無法察覺周遭發(fā)生的事。他們出生在1927—1944年之間,*年長的在德國潰敗時也還不到十八歲。他們的童年回憶通常只有巴伐利亞的蒼翠牧野。許多人生活在帝國領袖的貝格霍夫山莊周邊受安全保護的范圍內(nèi),那里位于慕尼黑南方的上薩爾茨堡(Obersalzberg)山地,距離奧地利邊界不遠。這個領導人專用區(qū)是一個遺世獨立的禁區(qū),錯綜復雜的戰(zhàn)局和戰(zhàn)爭所導致的殘酷恐怖都被隔絕在外。而在戰(zhàn)后的許多年間,第三帝國的史實完全沒被列入德國學校的教綱。
他們的父母可是人間怪獸?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寫道:“無論我們?nèi)绾谓吡φ覍ぃ褪菬o法在艾希曼身上發(fā)掘出任何真正的妖魔成分,不過這么說的意思當然不是指那一切都只是家常便飯。”檢方想把他看成“有史以來*不正常的怪獸”,但阿倫特認為他不過是個“平庸的公務員”,“正常得嚇人”。1961年審理期間,一名精神科醫(yī)生表示,艾希曼“至少比檢查過他以后的我自己更正常”。阿倫特則寫道:“理查三世決定本著原則行惡,但艾希曼心中絕對沒有這種念頭。”艾希曼本人則宣稱他是個溫柔的人,受不了看到血。他甚至不是對猶太人懷抱病態(tài)恨意的狂熱分子,也不曾受害于任何形式的洗腦。他之所以成為那個時代*大的罪犯之一,是因為他全然缺乏思考力,而這跟愚蠢截然不同。這種缺憾的其他顯現(xiàn)方式是他沒有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能力——“基本上他只知道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以及他的記憶失常問題。艾希曼無法知道或感覺到自己犯下了罪惡,他完全失去道德意識。“他所做的事,他已經(jīng)做了,他并不打算否認這個事實(……)”阿倫特指出。“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說他對那些事有任何后悔之意”,因為他認為“懊悔是小朋友的玩意兒”。阿倫特認為,光是缺乏意識這件事就足以讓人成為歷史上“名列前茅”的罪犯。但無論如何,艾希曼至少犯了一個原罪,那就是放棄行使一切道德意識。
然而,那些罪人無不希望將自己視為具有道德良知的人。海因里希•希姆萊雖然身為“*終解決方案”的策劃者,但他堅決相信自己是個有道德的人。哈拉爾德•韋爾策在他的著作《執(zhí)行者》(Les Exécuteurs)中強調(diào),在第三帝國統(tǒng)治時期,殺人行為被納入社會常態(tài)。國家社會主義特有的殺人道德觀讓那些死亡命令執(zhí)行者在殺人的同時得以維持“正確”的姿態(tài)。這一切在我們眼里雖然荒誕無比,但根據(jù)第三帝國的規(guī)范模式,為了德國的生存,殺人是必要的行為,而殺人的立論基礎是人類之間的絕對不平等。
本書所描繪的納粹孩子們透過一個再次變動過的規(guī)范及道德架構評斷他們父親的所作所為。有些人將父親的行為合理化或加以辯解,認為在他們所屬的規(guī)范架構中,他們的父親是以合法方式行動。希特勒時期的外交部部長馮•里賓特洛甫(von Ribbentrop)有一個兒子毫不遲疑地表示:“我父親只是在做他認為對的事。假如現(xiàn)在我們處在同樣的情況中,我會作出跟他一樣的決定。他只是希特勒的一個顧問,而事實上希特勒不會接受任何人的指導。我父親只希望一件事,那就是盡他身為德國人的義務。他早就預料到巨大危險正從東方降臨,歷史證明他是對的。”歌德倫•希姆萊的立場相同,終其一生她都認為她的父親海因里希•希姆萊“無罪”。希姆萊自己在紐倫堡大審判時想必也會說一樣的話,只不過他在審判開始以前就自殺身亡了。
美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吉爾伯特曾在紐倫堡大審判期間研究德國主要戰(zhàn)犯的案例,他認為那些人有一個共同特質,就是對他人缺乏同理心。他發(fā)現(xiàn)那些劊子手陷入憂郁的情況比被害者少,因為他們深信自己是別無選擇的好人。
等到他們的孩子必須面對過去時,情況并不見得如此。這些納粹的子女得知家庭的過往內(nèi)幕時,戰(zhàn)爭已經(jīng)結束,納粹異端已被消除,“解決猶太人問題”的論調(diào)已經(jīng)永遠失去合法性。
他們經(jīng)常是根據(jù)自己的童年經(jīng)驗去處理那個過往。有些人在孩提時代得到所有情感上的滿足,兒子如此,獨生女更是如此,例如海因里希•希姆萊的唯一婚生女歌德倫•希姆萊,納粹帝國元帥之女艾妲•戈林,或帝國理論家、德占俄國領土事務部部長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Alfred Rosenberg)的女兒伊雷妮•羅森貝格(Irene Rosenberg)。身為備受寵愛的掌上明珠,她們一輩子都相當認同納粹,并無條件崇拜她們的父親。許多納粹后代認為他們自己的故事比某某其他納粹要員小孩的故事容易承擔。這種看待方式相當詭異,仿佛他們相信這種家庭傳承可以量化。
為了更好地領會這些孩子們的個別故事,我們會說明每一位父親在國家社會主義政權中占有什么地位,他們的子女是如何浸淫在那個時代的理想中,以及他們的母親在他們的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了了解他們,我們必須以*近距離檢視他們童年時期的家庭環(huán)境。
某些第三帝國核心人物的后代在本書中缺席。在此我們不禁想到納粹帝國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的六個小孩,他們都在*高領導人的地堡中遭父母殺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瑪格妲•戈培爾的孫女,也就是她跟**任丈夫金特•匡特(Günther Quandt)所生兒子的女兒。這名孫女在二十四歲那年皈依猶太教,她的**任丈夫——一名猶太裔德國商人——曾經(jīng)被關進集中營。
至于*高領導人希特勒,他自己沒有留下后代。他曾說:“要是我有小孩的話,那多麻煩!那些人到*后一定會讓我的兒子繼位。可是像我這種人絕不可能生出健全的兒子。我們這種人幾乎一直都是這樣。看看歌德的兒子吧,廢人一個!”
七十多年后,針對這個主題進行書寫依然困難重重。在撰寫這本書的整個過程中,我一直避免對這些孩子們下道德判斷。他們不應該被認為必須為他們沒有犯下的惡行背負罪責,就算其中一部分人完全不會對父母的所作所為表示不以為然。那是不是他們面對一個無法承受的過去時所采取的一種防御“自我”的行為?
歌德倫•希姆萊的例子完美說明了這點。
納粹的孩子們 目錄
引言
歌德倫•希姆萊:納粹政權的“小娃娃”
艾妲•戈林:“納粹德國尼祿皇帝的小公主”
沃爾夫•R.赫斯:活在“*后戰(zhàn)犯”的陰影中
尼克拉斯•法郎克:渴求真相的總督之子
馬丁•阿道夫•鮑曼:帥俊的“小王儲”
霍斯的子女:奧斯維辛指揮官的下一代
施佩爾的子女:“惡魔工程師”的后裔
羅爾夫•門格勒:“死亡天使”之子
豈止是德國的故事?
致謝
注釋
納粹的孩子們 節(jié)選
引言
歌德倫、艾妲、馬丁、尼克拉斯,還有其他那些孩子們……
他們是希姆萊、戈林、赫斯、法郎克、鮑曼、霍斯、施佩爾、門格勒的小孩。這些孩子活在沉默中,他們的父親是罪犯,必須為當代歷史中*黑暗的年代負責。
可是歷史并不等同于他們的故事。
他們的父親罪大惡極,徹底泯滅天良。在紐倫堡大審判中,面對相關指控,他們的父親異口同聲,毫不猶豫地申辯無罪。但歷史是否記得,這些人也是為人父者?大戰(zhàn)結束后,在一種消除罪惡感的集體欲望中,某些人主張人民無辜,設法將納粹德國的殘暴及種族滅絕行徑完全歸咎于第三帝國的主要領導人物。至于那些受審的要人及其他許多納粹分子,為了逃脫罪責,他們會強調(diào):“那一切都是因為希特勒……”
那么,這本書里談到的孩子們,他們又有什么樣的人生歷程?他們繼承了一個共同的包袱:他們的父母消滅了數(shù)以百萬計的無辜人民。他們的名字被永遠蓋上可恥的烙印。
人是否應該覺得自己必須為父母所犯的罪行負責,甚至因此感到愧疚?家庭背景在我們的年少歲月中無法挽回地形塑了我們。盡管社會上的普遍認知是父母犯的錯不該由子女背負責任,但當一個人傳承到那么可怕的包袱,他不可能不受影響。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為人父者有兩條命,自己的命和兒子的命”,“龍生龍,鳳生鳳……”那些納粹要人的孩子們后來成了什么?他們怎么承受那么陰森恐怖的家庭遺產(chǎn)?
一名不知悔改的納粹曾經(jīng)對訪問他的猶太裔以色列外孫女說:“覺得自己有罪的人,就是有罪的人!”然后他泰然自若地給了她忠告:“跟那一切保持距離,這樣人生會簡單許多。”
要這些孩子們評斷他們的父母是非常困難的事。對于生育我們、撫養(yǎng)我們的父母,我們?nèi)狈陀^評斷所需的距離。情感聯(lián)結越是密切,道德判斷就越不容易。無條件認同,或者全面排斥?當家庭的過往如此駭人,我們?nèi)绾巫蕴帲窟@些納粹要人的兒女們有各自的立場,有些徹底反對父母,有些則與父母口徑一致,但很少有人采取中立態(tài)度。有些人一方面堅決摒棄父輩的作為,一方面卻能找到辦法繼續(xù)愛他們的父親。有些人永遠不可能愛一個“怪獸”,因此他們在內(nèi)心全盤否認那個黑暗面,借此維持一種無條件的孝心。另外還有一些人陷入對父親的排斥和仇恨。他們繼承到的過去宛如沉重的腳鐐,他們必須在日常生活中承受它,不可能對它視而不見。有人決定承認一切,有人走上心靈宗教的道路,甚至有人為免“遺傳罪惡”,決定結扎,或者透過自瀆的方式贖罪。否認、壓抑、認同、愧疚,所有人都得設法找到能讓他們面對過去的途徑,無論他們是否清楚意識到自己在做這件事。
這些孩子們大部分(曾經(jīng))生活在德國。其中有些皈依宗教,甚至成為天主教神甫或猶太教拉比。這么做是不是為了驅邪,借此解除身為罪犯之子的命運魔咒?舉阿倫·希爾-雅許夫(Ahron Shear-Yashuv)的例子,雖然他的父親并不是納粹政權的高官或重要執(zhí)行者,但他還是決定成為以色列軍的拉比。阿倫的本名是沃爾夫岡·施密特(Wolfgang Schmidt),他在修讀神學期間決定不要當天主教神甫,因為他不贊同天主教教義。他強調(diào),猶太大屠殺只是促使他皈依猶太教的部分原因,并且表示“猶太教在某些方面的確有迥異于其他宗教的特殊性,但寬宏大量也是它的特質。確實,皈依者不只會受到接納,他甚至有機會擔任拉比,在以色列國防軍當隨軍神甫及指揮官”。本古里安大學心理學教授丹·巴爾-昂(Dan Bar-On)認為這種類型的皈依旨在加入“受害者社群,擺脫歸屬于罪犯社群的心理負擔”。這種做法是不是在逃避過去,而不是勇敢面對它?皈依者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會給出各種不同回答。不過,宗教的洗禮確實讓某些人得以克服個人背景的重擔。
戰(zhàn)后力求復興的德國設法借由緘默驅魔,處在那樣的氛圍中,納粹的后代必須對自己做許多心理建設,才能讓自己站起來。
我在我外公生前跟他很親,他曾在德國空軍當職業(yè)軍人,住在黑森林深處的一棟狩獵小屋。他一輩子都不愿跟我提他生命中的那個階段。而且不是只有他這么做。在許多年間,戰(zhàn)爭的沉默身影飄蕩在德國和法國上空。戰(zhàn)爭的夢魘至今揮之不去,但人們愿意開口說話了。我小時候,所有人都屈服于沉默的宰制。跟我的外祖父一樣,戰(zhàn)后的幾個世代人們一直避免談論這個議題。某些人后來甚至采取啞巴策略,對那個時代只字不提,因為他們害怕玷污父母在他們心中的形象。這些人是否真的想知道他們的父母是什么樣的人,以及他們在德國歷史上那個黑暗時期涉入得有多深?答案是不見得。記憶并未傳承。為了逃避那個過去,我的德國母親在二十歲時選擇獨自到法國生活。她一直想要成為法國人,而當我開始著手寫這本書時,她的反應是不解。為什么處理這樣的題材?為什么繼續(xù)談這件事?這些都是我們不常問的問題。
我有德國、法國、俄國這三重家世背景,其中德國這個部分對我的人格施加了獨特的影響。德國的歷史被強加在我的生命中。安娜·韋伯曾說:“那是不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負擔?它從*初就存在,而且不會消失;沒有一個俄國人能代表古拉格,沒有一個法國人能代表法國大革命或殖民主義,他們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民族歷史。”然而,德國和納粹卻被畫上等號。
我對社會邊緣人的興趣促使我研究監(jiān)獄,然后成為刑事律師。這個職業(yè)為我?guī)韺懽鞅緯璧膰乐敹取辽傥沂沁@么希望——讓我憑借它援引歷史事實,以及探討書中所提的納粹孩子們對那些事實的觀感。透過他們的案例,我設法理解我們的過去在這個我們不顧一切想要取得主體性的世界中代表著什么。
真相與現(xiàn)實有時是非常沉重的負擔。有人傾向尊重家庭的秘密,即使導致那些秘密形成的人并非他們的家人。此外,毫無疑問的是,那些納粹要員沒有勇氣和力量向孩子們吐露他們犯下的暴行。
納粹高官的小孩大部分都不希望變更姓氏,這可能正是因為那個家姓無論如何也撇不開。某些人——例如阿爾貝特·施佩爾或馬丁·鮑曼的兒子——甚至冠上跟父親一樣的名字。赫爾曼·戈林的侄孫馬蒂亞斯·戈林說他喜歡自己的姓氏,其他一些人則表示姓氏無關緊要,繼承到什么姓就是什么姓。艾希曼的兒子表示:“逃避這個姓氏無法使問題改變,人不可能逃脫他的過去。”還有另外一些人——例如歌德倫·希姆萊和艾妲·戈林——對自己的父姓感到驕傲,而且非常景仰他們的父親。
奧斯維辛集中營指揮官魯?shù)婪颉せ羲乖?jīng)宣稱:“即使我是在執(zhí)行滅絕措施,我一樣過著正常的家庭生活……對我而言,家庭是神圣的,我跟它之間的聯(lián)結無法分割。”我們要如何理解這種矛盾?精神分裂的概念代表兩種互相矛盾的潛在可能性共存于自我中,這個概念可以用來解釋那些執(zhí)行命令者何以能夠一方面過著正常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卻屠殺數(shù)百萬人民。這種怪物怎么有辦法在親吻自己的小孩以后,走出家門殺害或命令別人殺害無數(shù)男女老少,毫無人性可言?我們該如何描繪希姆萊這號人物,想象他抱著他的“小娃娃”親吻,然后前往指揮部簽署命令處決兒童,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
輿論期望我們在那些罪犯身上識別出特定疾病,用來解釋他們的殘酷行為。但研究這個主題的人從來無法成功找出那些執(zhí)行命令者有什么獨有的人格。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時,一名負責檢查他的精神科醫(yī)生指出,艾希曼對妻子、兒女、父母、兄弟姐妹及朋友的行為“不只是正常,而且絕對值得嘉許”。我們寧愿相信那些人是一群嗜血怪獸,因為他們的“正常性”顯得更加令人毛骨悚然。普里莫·萊維曾說:“怪獸確實存在,但他們的數(shù)量太少,因此不至于構成真正的危險,比較危險的反而是所謂的普通人。”
在漢娜·阿倫特受人爭議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作者闡述了“惡的平庸性”這個概念,并描繪出一個小公務員的圖像,他充滿干勁但平庸至極,不懂得思考,無法分辨善惡。阿倫特沒有為他辯解,只是用他的例子強調(diào)非人性的因子存在于所有人身上,我們都必須不斷地“思考”,絕不能舍棄理性,要永遠保持質疑精神,才不會陷入惡的平庸性中。
本書所述及的納粹孩子們原本只知道他們父親的人格中的一個面向,另外那個面向是在德國戰(zhàn)敗后才被帶進他們的視野。大戰(zhàn)期間,他們年紀還太小,無法理解甚至無法察覺周遭發(fā)生的事。他們出生在1927—1944年之間,*年長的在德國潰敗時也還不到十八歲。他們的童年回憶通常只有巴伐利亞的蒼翠牧野。許多人生活在帝國領袖的貝格霍夫山莊周邊受安全保護的范圍內(nèi),那里位于慕尼黑南方的上薩爾茨堡(Obersalzberg)山地,距離奧地利邊界不遠。這個領導人專用區(qū)是一個遺世獨立的禁區(qū),錯綜復雜的戰(zhàn)局和戰(zhàn)爭所導致的殘酷恐怖都被隔絕在外。而在戰(zhàn)后的許多年間,第三帝國的史實完全沒被列入德國學校的教綱。
他們的父母可是人間怪獸?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寫道:“無論我們?nèi)绾谓吡φ覍ぃ褪菬o法在艾希曼身上發(fā)掘出任何真正的妖魔成分,不過這么說的意思當然不是指那一切都只是家常便飯。”檢方想把他看成“有史以來*不正常的怪獸”,但阿倫特認為他不過是個“平庸的公務員”,“正常得嚇人”。1961年審理期間,一名精神科醫(yī)生表示,艾希曼“至少比檢查過他以后的我自己更正常”。阿倫特則寫道:“理查三世決定本著原則行惡,但艾希曼心中絕對沒有這種念頭。”艾希曼本人則宣稱他是個溫柔的人,受不了看到血。他甚至不是對猶太人懷抱病態(tài)恨意的狂熱分子,也不曾受害于任何形式的洗腦。他之所以成為那個時代*大的罪犯之一,是因為他全然缺乏思考力,而這跟愚蠢截然不同。這種缺憾的其他顯現(xiàn)方式是他沒有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能力——“基本上他只知道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以及他的記憶失常問題。艾希曼無法知道或感覺到自己犯下了罪惡,他完全失去道德意識。“他所做的事,他已經(jīng)做了,他并不打算否認這個事實(……)”阿倫特指出。“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說他對那些事有任何后悔之意”,因為他認為“懊悔是小朋友的玩意兒”。阿倫特認為,光是缺乏意識這件事就足以讓人成為歷史上“名列前茅”的罪犯。但無論如何,艾希曼至少犯了一個原罪,那就是放棄行使一切道德意識。
然而,那些罪人無不希望將自己視為具有道德良知的人。海因里希·希姆萊雖然身為“*終解決方案”的策劃者,但他堅決相信自己是個有道德的人。哈拉爾德·韋爾策在他的著作《執(zhí)行者》(Les Exécuteurs)中強調(diào),在第三帝國統(tǒng)治時期,殺人行為被納入社會常態(tài)。國家社會主義特有的殺人道德觀讓那些死亡命令執(zhí)行者在殺人的同時得以維持“正確”的姿態(tài)。這一切在我們眼里雖然荒誕無比,但根據(jù)第三帝國的規(guī)范模式,為了德國的生存,殺人是必要的行為,而殺人的立論基礎是人類之間的絕對不平等。
本書所描繪的納粹孩子們透過一個再次變動過的規(guī)范及道德架構評斷他們父親的所作所為。有些人將父親的行為合理化或加以辯解,認為在他們所屬的規(guī)范架構中,他們的父親是以合法方式行動。希特勒時期的外交部部長馮·里賓特洛甫(von Ribbentrop)有一個兒子毫不遲疑地表示:“我父親只是在做他認為對的事。假如現(xiàn)在我們處在同樣的情況中,我會作出跟他一樣的決定。他只是希特勒的一個顧問,而事實上希特勒不會接受任何人的指導。我父親只希望一件事,那就是盡他身為德國人的義務。他早就預料到巨大危險正從東方降臨,歷史證明他是對的。”歌德倫·希姆萊的立場相同,終其一生她都認為她的父親海因里希·希姆萊“無罪”。希姆萊自己在紐倫堡大審判時想必也會說一樣的話,只不過他在審判開始以前就自殺身亡了。
美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吉爾伯特曾在紐倫堡大審判期間研究德國主要戰(zhàn)犯的案例,他認為那些人有一個共同特質,就是對他人缺乏同理心。他發(fā)現(xiàn)那些劊子手陷入憂郁的情況比被害者少,因為他們深信自己是別無選擇的好人。
等到他們的孩子必須面對過去時,情況并不見得如此。這些納粹的子女得知家庭的過往內(nèi)幕時,戰(zhàn)爭已經(jīng)結束,納粹異端已被消除,“解決猶太人問題”的論調(diào)已經(jīng)永遠失去合法性。
他們經(jīng)常是根據(jù)自己的童年經(jīng)驗去處理那個過往。有些人在孩提時代得到所有情感上的滿足,兒子如此,獨生女更是如此,例如海因里希·希姆萊的唯一婚生女歌德倫·希姆萊,納粹帝國元帥之女艾妲·戈林,或帝國理論家、德占俄國領土事務部部長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Alfred Rosenberg)的女兒伊雷妮·羅森貝格(Irene Rosenberg)。身為備受寵愛的掌上明珠,她們一輩子都相當認同納粹,并無條件崇拜她們的父親。許多納粹后代認為他們自己的故事比某某其他納粹要員小孩的故事容易承擔。這種看待方式相當詭異,仿佛他們相信這種家庭傳承可以量化。
為了更好地領會這些孩子們的個別故事,我們會說明每一位父親在國家社會主義政權中占有什么地位,他們的子女是如何浸淫在那個時代的理想中,以及他們的母親在他們的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了了解他們,我們必須以*近距離檢視他們童年時期的家庭環(huán)境。
某些第三帝國核心人物的后代在本書中缺席。在此我們不禁想到納粹帝國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的六個小孩,他們都在*高領導人的地堡中遭父母殺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瑪格妲·戈培爾的孫女,也就是她跟**任丈夫金特·匡特(Günther Quandt)所生兒子的女兒。這名孫女在二十四歲那年皈依猶太教,她的**任丈夫——一名猶太裔德國商人——曾經(jīng)被關進集中營。
至于*高領導人希特勒,他自己沒有留下后代。他曾說:“要是我有小孩的話,那多麻煩!那些人到*后一定會讓我的兒子繼位。可是像我這種人絕不可能生出健全的兒子。我們這種人幾乎一直都是這樣。看看歌德的兒子吧,廢人一個!”
七十多年后,針對這個主題進行書寫依然困難重重。在撰寫這本書的整個過程中,我一直避免對這些孩子們下道德判斷。他們不應該被認為必須為他們沒有犯下的惡行背負罪責,就算其中一部分人完全不會對父母的所作所為表示不以為然。那是不是他們面對一個無法承受的過去時所采取的一種防御“自我”的行為?
歌德倫·希姆萊的例子完美說明了這點。
歌德倫·希姆萊:納粹政權的“小娃娃”
歌德倫·希姆萊:納粹政權的“小娃娃”從1958年開始,奧地利波希米亞森林中的一個小村鎮(zhèn)每年都會接待一群懷念德意志第三帝國的人。他們來自歐洲各地,每年秋天匯聚在這個古代曾經(jīng)是凱爾特人圣地的美麗鄉(xiāng)村。已經(jīng)有相當年紀的男子穿上*體面的衣服,到這里跟從前的伙伴們聚首;年輕的新納粹分子也會趕來湊熱鬧,認識一些前輩。在這個由老一輩納粹黨人和新生代親極右派人士組成的小型集會上,所有人都認為當年的武裝黨衛(wèi)軍只是在盡他們的公民義務。在場民眾樂于贊美黨衛(wèi)軍的犧牲精神,有時甚至會將他們視為大時代的受害者。
在一家窗簾拉上的當?shù)乜蜅V校幻凶涌犊ぐ旱匾髡b偉大德意志的光榮。他喜歡像從前他的思想導師那樣激勵聽眾;他希望重塑當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啤酒館中演說時所觸發(fā)的那種如癡如狂的氣氛。數(shù)十年已然流逝,但與會者的理想堅定不移。有些人驕傲地佩戴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獲得的德國軍章——無論是“鐵十字”或“鐵十字騎士十字”勛章,中間一定都有一個納粹十字。他們興致勃勃地回顧德意志民族充滿優(yōu)越感的時代;那時全國團結一致,講求絕對的自我犧牲,對“內(nèi)部敵人”不抱任何人道情操。這個著魔般的小社群一本初衷,致力追求偉大,并服膺黨衛(wèi)軍的座右銘:“我們的榮耀名叫忠誠。”
這場集會的女性榮譽嘉賓不跟眾人打成一片。她與人群保持距離,偏好在一小群“朝臣”簇擁下,接見少數(shù)幾個有幸受邀拜見她的人。她神色凝重,被歲月侵蝕的臉孔顯出尖酸氣息,但她依然斗志高昂。她把纖細白發(fā)在后頸項上方系成發(fā)髻,襯衫上則神氣地別上銀質胸針——四個馬頭圍成一圈,勾勒出納粹十字的形狀。
掩藏在眼鏡后方的小眼睛散發(fā)冰冷的藍光,使她的交談對象感到畏懼。她受人寵愛,因為她是偉大德意志的首選傳人——“納粹主義的公主”歌德倫·希姆萊。
“公主”喜歡看到她的擁護者前來晉見,并用偵訊式的口吻問他們:“大戰(zhàn)期間你在哪里?”“你在哪個單位服務?”她的父親曾經(jīng)教導她軍事后勤業(yè)務,當他帶著她巡回各地督導業(yè)務時,她也善于從旁觀察。現(xiàn)在是當年那些軍人來接受她督察的時候,能有機會被引介給希特勒手下*優(yōu)秀執(zhí)行官的女兒,他們都感到無比驕傲。他們報出自己的身份及軍階時,感覺自己仿佛回到從前那個他們在世上享有權威的時代。在短暫的片刻中,這些日復一日被迫對自己的過去絕口不提的人終于找回了一些失落的豪氣。
“維京黨衛(wèi)軍第五裝甲師。”剛走進小客廳的男子面帶怯場的表情說。她繼續(xù)質問:“是自愿加入丹麥武裝黨衛(wèi)軍的嗎?”這位時年六十八歲的退伍軍人回道:“完全自愿。”他叫瓦格納·克里斯滕森(Vagner Kristensen),1927年出生于丹麥菲英(Fyn)島。在這名嬌小女子面前,他們?yōu)槭裁催@么充滿敬意,這么戒慎恐懼?長年間,無論父親是否在她身邊,她一直生活在他的庇蔭下,是否因此而不自覺地仿效了他的言行舉止、他的說話聲調(diào)?身為不負父親之名的好女兒,她的人生目標是為他平反。海因里希·希姆萊只有她這么一個婚生子女,他把她捧為掌上明珠,而她也懂得好好回報。
今天,歌德倫·希姆萊要接見的人還有原籍丹麥的澤倫·卡姆(Sren Kam),黨衛(wèi)軍編號456059。這名納粹分子涉及1943年一名反納粹記者的謀殺事件,但從未被定罪。他潛逃到德國,在巴伐利亞無憂無慮地度過余生。他雖然被列入頭號通緝納粹罪犯名單,但一直逍遙法外。歌德倫的父親生前必須一直努力設法克服他的自卑感和人際關系障礙,倘若今天他能看到女兒這樣自信十足地面對這些老納粹,他必定會感到非常驕傲。
年少時期的她因為害怕讓父親失望,會傾力央求母親向父親隱瞞她品行不良或胡鬧的事。她堅決相信父親是無辜的,她認為他并沒有犯下那些受世人指責的罪行,并將他被定罪判刑的事視為絕對的不公。長久從來,她一直想寫一本書,企圖為父親平反,但不是“辯護”,因為為他辯護無異于承認他有罪。歌德倫深信有朝一日,人們提到他的名字時,“會跟現(xiàn)在我們提到拿破侖、威靈頓或毛奇的情形一樣”。
但歷史無可挽回地定了他的罪。
星期三下午,她的父親有時會帶她一起去督導業(yè)務,特別是到德國的**個集中營——達豪(Dachau)視察。達豪集中營距離慕尼黑區(qū)區(qū)十來公里,是由他親自規(guī)劃建成,于1933年啟用。“佩戴紅色三角形的是囚犯,黑色的是罪犯。”他向她說明道。對這個小女孩而言,那些人的模樣通通都像犯人:衣著邋遢,胡須沒刮。她對菜園和溫室比較有興趣。她回憶當年往事:“我父親向我解釋種在那里的那些草本植物為什么重要,我還摘了一些葉子。”菜園讓她想起小時候在農(nóng)場生活的時光,那時她總喜歡到園子里當媽媽的幫手。達豪之行是她十二歲時的事,一張留存至今的照片見證了那個陰森可怕的參觀活動。身穿黑色大衣的金發(fā)小女孩面帶微笑,模樣相當快樂;圍繞在她身邊的人包括她的父親希姆萊、后來成為蓋世太保領導的萊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以及父親的侍從官卡爾·沃爾夫(Karl Wolff),沃爾夫上方的標牌則寫著那里是犯人的集合點。
歌德倫滿懷贊佩之情看著父親節(jié)節(jié)高升。1943年8月,她在日記中寫道:“可愛的爹地當了帝國內(nèi)政部部長,我欣喜若狂。”這位爹地是“多么顯赫”。1942年7月,海因里希前往奧斯維辛集中營檢視*終解決方案的具體建置——大規(guī)模使用齊克隆B毒氣的殺人作業(yè)。當時他在給夫人的一封信中若無其事地寫道:“我要去奧斯維辛一趟,我給你一個親親。你的海尼。”在他的書信中,他從不提供行程或從事活動方面的細節(jié),對滅絕猶太人的工作更是只字未提。他只是簡單說他工作繁忙,有重責大任在身。這樣一個人物后來對于他所犯下的殘酷罪行做了泰然自若的辯白:“關于猶太婦女和兒童,我不曾感覺自己有權利讓那些小孩長大成為充滿報復心態(tài)的殺手,任由他們荼毒我們的子孫。我認為那樣做是懦弱的行為。因此,這個問題的解決方式毫無妥協(xié)余地。”
黨衛(wèi)軍帝國統(tǒng)領海因里希·希姆萊無疑是第三帝國壓迫機制的狂熱操控者,但那段人類歷史并不是希姆萊的女兒所認同的歷史。海因里希·希姆萊的兒時玩伴曾說他小時候連一只蒼蠅都不肯傷害。但長大以后,他卻成為蓋世太保及武裝黨衛(wèi)軍的關鍵領導人物,主導集中營體制的建立以及歐洲猶太人的滅絕行動。
1927年間,他搭火車從慕尼黑前往靠近奧地利邊界的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時,在車上認識了歌德倫的母親瑪格麗特·西格羅特(Margarete Siegroth),她是一名離了婚的護士,娘家姓氏為博登(Boden)。這時的海因里希·希姆萊是個體弱多病的二十七歲青年,患有斜眼,下巴扁塌后縮,完全不符合“雅利安人種”的理想外形。海因里希對自己的外形感到自卑。由于他體質孱弱、消化系統(tǒng)不良,他既無法從事運動,在餐宴場合也不能盡興飲酒。身為軍人,他感到挫敗,于是轉而對紀律和軍服產(chǎn)生毫無節(jié)制的迷戀,并終于借此找到自己的立足點。年輕時代的他很少跟女性交往,以至于他甚至會提倡禁欲的益處。但后來,他又哀嘆自己年輕時無法享有更豐富的性愛生活。他到二十八歲才**次跟女人行房。小名“瑪嘉”的瑪格麗特金發(fā)碧眼、身材高挑,篤信基督新教,整個人非常符合雅利安女性的理想典型。為了博得佳人芳心,海因里希·希姆萊提供給她許多跟共濟會和“猶太人的全球陰謀”有關的書刊資料。當時的德國深陷經(jīng)濟危機,竭力尋求“救星”,并急著找到代罪羔羊;瑪嘉未能免于周遭的反猶聲浪。她認識希姆萊以后,決定賣掉她在任職診所中持有的股份,當時她這樣描述她的合伙人:“猶太人永遠都會是那副猶太德行。”
個性害羞的海因里希·希姆萊會寫情書給瑪嘉,有時喜歡署名為“你的國土傭仆”。瑪嘉在回信中說:“我們要一起幸福才行。”他們的結合主要是基于一種親昵的情感,但不是愛情。瑪嘉比她大七歲,希姆萊的家人從來不曾接納她。希姆萊出身于天主教家庭,他的母親的信仰極為虔誠,但瑪嘉卻是個異類,她是個普魯士人,信的是新教,離過婚,而且性格焦慮不安,與社交場合格格不入。希姆萊的家人自忖:這樣一個女人難道不會損害家庭的名望?1928年7月3日,兩人在柏林舍恩貝格區(qū)結婚,希姆萊的家人均未到場。1929年8月8日,體重三千六百二十五克、身長五十四厘米的藍眼小女孩歌德倫呱呱墜地,成為海因里希·希姆萊的唯一婚生女,是他昵稱為“小娃娃”的掌上明珠。
歌德倫這名字是否援引自他在年輕時讀過而且深深喜愛的一本書——《歌德倫傳奇》?這本書歌頌北歐女性的美德,男人愿為這樣的女人赴湯蹈火。后來瑪嘉無法再幫海因里希生小孩,夫妻兩人于是決定收養(yǎng)一個男孩,是一名黨衛(wèi)軍陣亡軍人的兒子。但這個小男孩未能在新家獲得家庭的溫暖,瑪嘉曾在她的日記中說他具有“罪犯的本性”,擅于說謊,甚至是個小偷。后來他被送到寄宿學校,然后又轉到一間“納波拉”學習。納波拉(Napola)是“National politische Lehranstalt”(國立政治教育機構)的縮寫,這是德意志帝國訓練國家精英的地方。至于歌德倫,她完美無瑕地扮演模范女兒的角色,她的母親則三番五次在日記中提到她有多乖巧、多討人喜歡:“‘小娃娃’是個乖寶寶,是愛的化身。”她也曾提到德國將波蘭德意志化的行動:“我把新聞念給她聽,并對她說明那代表的意思是:派軍隊重回祖國。這是個前所未聞的壯舉,一千年后世人都還將對此津津樂道。”
1928年,海因里希·希姆萊在慕尼黑大學修完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學位以后,用妻子的陪嫁財產(chǎn)買下慕尼黑郊區(qū)瓦爾特魯?shù)铝?Waldtrudering)的一座養(yǎng)雞場。夫妻兩人向往農(nóng)業(yè),希姆萊原本打算跟妻女在那里快樂生活。事實上,他的妻子大都是獨自跟女兒歌德倫待在農(nóng)場中。瑪格麗特肩負管理整座養(yǎng)雞場的重任,但母雞下的蛋不多,小雞紛紛死亡,破產(chǎn)的陰影迅速降臨。瑪格麗特的心情越來越低落,她抱怨丈夫經(jīng)常出差,而且到后來,希姆萊變得幾乎完全沒時間返回家門。丈夫離家越遠,瑪嘉的脾氣就越暴躁,她變得充滿鄙夷心態(tài)和攻擊性。1933年,希姆萊夫妻將農(nóng)場變賣,搬到慕尼黑市區(qū)居住。希姆萊長期被納粹高層視為“老實的小伙子”“心地善良但可能意志不堅”,這時的他其實已經(jīng)當上政治警察總長,然后又正式被任命為隸屬于內(nèi)政部的全國警察總長,主掌德意志帝國警政機制,直到1936年6月為止。黨衛(wèi)軍帝國統(tǒng)領海因里希·希姆萊是個冷酷無情、精于算計的審訊者,阿爾貝特·施佩爾曾說他是“半個有板有眼的小學教員,半個異想天開的瘋子”;通過對種族純粹論的偏執(zhí),這號人物終于為自己的各種自卑情結找到宣泄及報復的出口。
1936年及1937年間短暫居住在慕尼黑以后,希姆萊一家人遷居到上巴伐利亞特格爾恩湖(Tegernsee)畔小鎮(zhèn)格蒙德(Gmund)。1934年間,希姆萊就在那里買了一棟房子。但他在黨內(nèi)的職責越來越繁重,妻子也愈來愈常獨守空閨。他重新開始性生活,對社會中各式各樣的性愛活動興致勃勃。他承認瑪嘉無法幫他生更多小孩并不是她的錯,但他并不打算對這種情況俯首認命。對他而言,一夫一妻制是“撒旦的杰作”,那是天主教會發(fā)明的產(chǎn)物,必須予以廢除。他以日耳曼史前文化為自己的立論基礎;早年那些種族高貴的日耳曼人為了能有小孩,可以自由重婚。基于這樣的理念,他允許手下所有碰到夫妻問題的軍官離婚或跟其他女人婚外同居。他認為正常男人不可能以一輩子跟同一名女人行房為滿足,而且只有在一夫二妻的情況下,兩個女人才會設法尋求自我超越。此外,由于戰(zhàn)爭期間生育率趨于降低,對某些黨衛(wèi)軍領導干部而言,一夫二妻或多重配偶的制度也是一種維持生育率的手段。因此,雖然第三帝國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的妻子為他生了六個小孩,但他在跟她結婚以前,就約法三章說婚后他要繼續(xù)享有婚外關系。在同樣的“時代氛圍”中,納粹黨黨務中心領導人、希特勒親信馬丁·鮑曼的妻子在為他產(chǎn)下十名子女后,自愿為了“報國”而設計出一套生活方式,讓丈夫的情婦們跟她一起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她的目標是:“將所有孩子們集結在湖邊的房子里,大家一起生活。”鮑曼夫妻堅信國家必須制定法律,讓“堂堂正正的健康男子漢合法擁有兩名妻子……有那么多好女人迫于現(xiàn)實,不能(合法地)生小孩……我們也需要這些女人的小孩!”鮑曼希望廢除“私生子”這種字眼,以及禁用“私通”“婚外情”這類帶有貶義的詞語。為了改善生育率下降的問題,海因里希·希姆萊提倡將婚外生育合法化,甚至鼓勵這種做法。于是納粹政府從1936年開始成立所謂的“生命之泉”(Lebensborn),也就是專為雅利安婦女而設、以實踐種族優(yōu)生理論為宗旨的生育中心。這些機構接納單身女性,并為她們保守生小孩的秘密。此外,為了避免同性戀愛發(fā)生,希姆萊倡議舉辦青少年聚會活動。1937年2月18日,他在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麓的巴特特爾茨溫泉鎮(zhèn)針對同性戀議題發(fā)表演說時表示:“我認為有必要確保十五六歲的少年能通過舞蹈課、交誼晚會及其他各種活動認識女生。實驗已經(jīng)證明,十五歲或十六歲的年輕男孩身心正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如果他能找到令他心動的舞伴,或談一場浪漫的青春戀情,他就得救了,他就遠離危險了。”聽到希姆萊這席話,我們很難想象他在年輕時竟然曾經(jīng)主張禁欲。1940年,希姆萊跟瑪嘉分居,但為了尊重這位替他生下寶貝女兒的女人,他決定不跟她離婚。接下來,他一直竭力確保自己跟女兒維持非常親近的關系,那是他在世間*心愛的人。盡管他在政界的職責與日俱增,差旅頻繁,但他一直盡力當個好爸爸、好丈夫。歌德倫喜歡把父親稱作“旅行爸”,在她的許多兒時照片中,這位黏在父親身邊的“小娃娃”是個完美的德國小女孩,金發(fā)碧眼,臉蛋如天使般天真無邪,身穿巴伐利亞傳統(tǒng)服裝,頭發(fā)通常扎成辮子,有時則是在兩側卷成馬卡龍狀圓辮。她的父親經(jīng)常跟她分享生活中的事,寄他的照片給她看,并盡可能抽空陪伴她。只要翻閱海因里希·希姆萊的行事歷,就可以看到他幾乎每天都會跟妻子和女兒通電話。希姆萊巨細靡遺地記錄他的生活,他的本子里除了公務項目,也充滿令人驚奇的生活點滴,例如“跟孩子們玩耍”或“跟小娃娃聊天”。“小娃娃”如果成績不好,他會非常生氣。對他而言,服從、整潔及學業(yè)是兒童教育的核心要素。他自己小時候不也對大人展現(xiàn)出無懈可擊的順從?他一直是個好學生。至于瑪嘉,她在女兒出生后不久,就開始為她寫童年記事本,通過里面許許多多的記載,我們看到小女兒的良好行為表現(xiàn),超乎同齡小孩的整潔程度,以及瑪嘉在設法讓女兒順從的過程中遭遇的困難等。父親回來看女兒時,會帶她一起到森林里打獵,兩人在林間悠閑漫步。小女兒很喜歡采花和收集苔蘚。
德意志帝國元首在歌德倫的童年生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1935年,希特勒就任總理兩年后,某天夜里小女孩睡不著覺,她焦慮地問媽媽:“希特勒伯伯以后也會死掉嗎?”媽媽設法安撫女兒,并向她保證希特勒大統(tǒng)領會長命百歲,歌德倫松了一口氣,然后回道:“媽咪,不對,我知道他會長命兩百歲。”希特勒對這個小妹妹關愛有加,令希姆萊夫婦感到既開心又榮幸。瑪嘉·希姆萊在1938年5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元首到家里來了,‘小娃娃’超興奮。難得跟他私底下同桌小聚,實在太美妙了。”
每年元旦,歌德倫都會見到帝國領袖,這位大伯伯則會送她一個洋娃娃或一盒巧克力。
1936年,一位名叫赫德薇格·波特哈斯特(Hedwig Potthast)的女秘書進入希姆萊的部門服務,希姆萊從1938年底開始跟她發(fā)展婚外情。他決定告知他的妻子,免得萬一自己跟情人生下小孩,到時也是紙包不住火。希姆萊在1940年公開表態(tài)支持推行婚外生育的政策,隨后他身體力行,跟情婦孕育出兩個小孩,分別是1942年出生的兒子赫爾格(Helge)和1944年出生的女兒娜奈特·朵羅泰雅(Nanette Dorothea)。小男孩的日耳曼名字原意為“種族純粹的圣人”,但這個小孩完全沒有希姆萊期望自己的后代能具備的特質。他的健康狀況不良,患有皮膚病,而且羞怯到近乎病態(tài)的程度。
1942年,希姆萊將他的第二個家庭安置在“雪角莊園”,這棟大宅位于巴伐利亞南部的舍瑙(Schnau),距離納粹帝國領袖的地盤貝希特斯加登不遠。赫德薇格·波特哈斯特和兩名子女在那里一直待到同盟國占領德國為止。赫德薇格答應在希姆萊的陰影中默默生活,心中盼望著大戰(zhàn)結束后有朝一日能跟他團圓。在同盟國眼中,赫德薇格是“納粹女性的樣板典型”。她的性格跟瑪嘉截然不同,是個快活而可愛的女人,跟希姆萊身邊的人能維持良好關系。瑪嘉得知丈夫出軌時,在日記中無可奈何地寫道:“男人都是在有錢有名以后才會想到做這種事。假如丈夫沒錢沒名,反倒是逐漸年邁的妻子必須幫助他們養(yǎng)活自己,以及容忍他們。”不過在她跟丈夫的通信中,我們完全找不到跟這名情婦和她的子女有關的記述。
歌德倫經(jīng)常孤單一人。父母不在身邊時,負責照顧她的是她的阿姨莉蒂亞·博登(Lydia Boden)。1939年起,她的母親為了報效社會,決定到柏林重拾護士工作,特別是在紅十字會。有時她會前往德軍占領區(qū),例如1940年她奔赴波蘭,并在日記中寫下一些評論:“這群波拉克猶太鬼子大都面目可憎,完全不像人類,更甭提那無可名狀的污穢。要整頓這片臟亂真是空前絕后的艱巨任務。”還有:“這個波蘭民族不太容易因為傳染病而死,他們都有免疫能力。真令人難以理解。”
至于歌德倫,她很少離開格蒙德。1945年9月22日,她在紐倫堡接受審問時表示:“大戰(zhàn)期間我們從來不曾出行。整整五年我們都住在那棟房子里,我天天上學,那是我唯一做的事。”的確,希姆萊不肯讓寶貝女兒跟媽媽一起搬到柏林居住,他生怕盟軍空襲會變得更加猛烈。“小娃娃”不斷引頸盼望父母歸來,她特別期待的是父親偶爾短暫出現(xiàn)在家里的時刻。她經(jīng)常鬧胃痛,是個緊張兮兮的小女孩,在校成績越來越差。不過她密切關注戰(zhàn)況發(fā)展,擔心父親的安危。她的母親曾在日記中提到,女兒聽到許多她不該知道的事。不過她的父親希望妻子能對她說明局勢,盡管以小女孩的年紀而言,她還無法完全明白那些事。1941年6月22日是個星期天,希特勒在這天發(fā)動“巴巴羅薩行動”,正式開啟東方戰(zhàn)線,當時十二歲的歌德倫在寫給父親的信中說:“我們跟蘇聯(lián)打仗實在太可怕了,畢竟他們曾經(jīng)是我們的盟友啊!而且蘇聯(lián)那么那么那么大,假如我們拿下整個蘇聯(lián),想必戰(zhàn)斗會非常艱難。”
看來歌德倫似乎聽說過納粹帝國領導干部的瘋狂迷夢——建立直抵烏拉爾山的德意志生存空間。1943年11月1日,她在日記中寫道:“爸爸媽媽又再買了一大塊花園用地。在溫室后面,一直往上到森林的地方……犯人已經(jīng)把原來的花園圍籬移走了。等到天下太平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在東方有一棟房產(chǎn),那棟房產(chǎn)會替我們生出更多錢,然后我們就可以翻修格蒙德的房子。這樣一來,走道就可以變得更亮,我們的房間也會變得更大。沒錯,林登費希特(Lyndenfycht)的房子以后會變成我的。和平來到以后,我們也可以住進內(nèi)政部。也許我們在上薩爾茨堡還會有一棟房子。對,這一切只等著和平來到,不過那還得等很久很久(兩三年)。”
1944年7月,她聽到德國戰(zhàn)敗的消息。雖然她先前已經(jīng)聽說諾曼底登陸和蘇軍進逼德國邊境的事,但她一直設法提振自己的信念:“可是所有人都那么相信我們會勝利,我身為爸爸的女兒,知道他目前備受器重,地位越來越崇高,我也必須相信這件事,而且我是真心誠意地相信。我方戰(zhàn)敗是完全無法想象的事。”同一個月間,希姆萊出動達豪集中營“格蒙德外部突擊隊”的囚犯,在自家花園中興建一座防空地堡。
歌德倫的玩伴很少。她的母親跟夫家和娘家的人都不合,唯一處得來的人只有她自己的姐妹莉蒂亞。歌德倫獨自跟脾氣日益暴躁的母親朝夕相處,感到非常痛苦。后來她的幾個堂兄弟[也就是海因里希的哥哥格布哈特·希姆萊(Gebhard Himmler)的兒子們]來到格蒙德,跟她生活在同一棟房子中,結果母親跟伯母之間的沖突為這群堂親之間的關系投下陰影。歌德倫在當時的日記中提到,母親幾乎無法忍受身邊的任何人。在整個大戰(zhàn)及納粹潰退期間,一直到父親在1945年死亡,歌德倫見到父親的次數(shù)不超過十五次或二十次。希姆萊返家停留總是來去匆匆,頂多待個三四天;平時她盼望得到的只有父親打來的電話,還有他經(jīng)常寫給她的信(他會隨函附上題獻給她的照片)。另外,他還會寄包裹給家人,里面裝些衣服和巧克力、乳酪、糖果之類的食品。有一天,歌德倫接到父親從荷蘭寄來的一百五十朵郁金香。大戰(zhàn)快要結束時,民生物資變得更加稀少而難以取得,但希姆萊總有辦法寄送糧食給家人。1945年3月5日,歌德倫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在歐洲不再有盟友,現(xiàn)在一切只能靠自己了。而且國內(nèi)有太多人叛國。(……)整體氣氛低到零點。(……)我國空軍還是一樣爛。戈林只會吹牛皮,什么事都不管。戈培爾工作很拼,不過他老愛出風頭。所有人都一直在拿獎牌、領勛章,只有爸爸例外,而他才是**個該被褒揚的人。(……)全國人民都在注意他。他總是把身段放低,從不求凸顯自己。”
1944年11月,歌德倫在格蒙德*后一次見到父親,那次他返家跟她相聚了兩天。1945年3月,她*后一次通過電話聽到父親的聲音,然后在同年4月接到父親的*后一封信。父母之間的電話交談內(nèi)容不是關于日常生活,就是關于他的健康狀況惡化的事;許多年來,他的胃痛不斷復發(fā)。小女孩后來向同盟國人員表示:“我*后一次見到他時,他說他希望圣誕節(jié)時可以回家團圓,但他不能肯定。”1945年4月,由于美國大軍逼近,瑪格麗特不得不帶著女兒離開格蒙德,前往南方……希姆萊找達豪集中營的囚犯在自家游戲場建造的地堡已經(jīng)不足以提供保護了。
1945年5月13日,年方十五的歌德倫跟母親逃難到蒂羅爾地區(qū)南部、距離波札諾(Bolzano)不遠的山間村鎮(zhèn)沃肯斯坦(Wolkenstein),但在那里遭到逮捕。希姆萊的前任參謀長、黨衛(wèi)軍上級集團統(tǒng)領卡爾·沃爾夫將軍在他位于波札諾的豪華莊園中被捕時,他跟同盟國方面達成協(xié)議:“只要你們讓我回德國,我就告訴你們希姆萊的妻女在哪里。”經(jīng)過訊問之后,母女兩人被移送到一處豪華宅邸,那是一名前電影制片人的產(chǎn)業(yè),她們跟其他一些女犯人一起被囚禁在那里。然后她們又在波札諾的一家旅館度過兩天,接著被送到維羅納維待了一晚,再用飛機載到佛羅倫薩,一路上都有警衛(wèi)人員護送,以免她們受到民眾或游擊隊員攻擊。佛羅倫薩英國偵訊中心的一名警衛(wèi)信誓旦旦地告訴歌德倫和她的母親:“要是你們透露你們的姓氏是希姆萊,他們會把你們碎尸萬段。”偵訊開始進行。瑪格麗特的回話讓人覺得她一直被排除在丈夫的活動之外。一名英國軍官指出,她把自己封閉在“一種鄉(xiāng)下布爾喬亞婦女的心態(tài)”中。歌德倫對父親的活動同樣所知無幾。在被監(jiān)禁期間,她通過同盟國人員及外國報刊媒體重新認識了歷史。
然后她們又被帶到羅馬,詳細地點是意大利電影的殿堂——電影城制片廠,英國情報局在那里成立了一個資訊中心。海因里希·希姆萊的妻女是那里僅有的女性犯人,同盟國人員為她們布置了一間牢房,里面的裝設方式居然取材自一部法西斯宣傳影片!被關在這里四個星期以后,歌德倫決定絕食抗議糟糕透頂?shù)幕锸常痪盟纳眢w就變得虛弱,并開始發(fā)高燒。化名“布里奇”(Bridge)的英國情報單位指揮官請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翻譯,要他說服歌德倫進食。歌德倫沒有白白絕食,自此她和母親享有跟同盟國軍官一樣的伙食。接下來她們陸續(xù)轉往米蘭、巴黎及凡爾賽的監(jiān)獄,在凡爾賽待了三天,然后再被送到紐倫堡的監(jiān)獄。“從今以后我的姓氏就是希姆萊,”歌德倫這樣宣布,“不再使用假名,不再喬裝他人。”1946年間,她出席紐倫堡大審判,但她的出現(xiàn)沒有帶來任何效用,因為她一無所知。當她被問到是否會跟父親討論戰(zhàn)情時,她回道:“我跟我父親從來不談戰(zhàn)爭或其他類似的事。”
這時歌德倫依然不知道父親的下落。由于她的母親聲稱心臟有問題,負責管理拘留營的軍官們認為*好不要立刻告訴她幾天前——也就是1945年5月23日——她的丈夫已經(jīng)自殺身亡的事。在一次看診及搜身檢查時,他宣告一句“我的名字叫海因里希·希姆萊”,然后成功吞下事先含在口中的氰化物膠囊。雖然英國人立刻介入處理,并幫他洗胃,他還是在十二分鐘后斷了氣。
1945年7月13日,在接受美聯(lián)社記者安·斯特林格(Ann Stringer)采訪時,瑪格麗特聲言她知道丈夫以蓋世太保總長身份從事的活動;她宣稱自己對他感到驕傲,并強調(diào)“我們德國人不會問女人這種問題”。對于世人痛恨這位黨衛(wèi)軍統(tǒng)帥,她有何看法?“誰都不喜歡警察。”當斯特林格問到希姆萊被英軍擒拿以及他服用氰化物自殺的事時,瑪格麗特完全沒表現(xiàn)出任何激動或驚愕之情;她只是雙手交叉,聳了聳肩。這位美國記者說她從未采訪過那么冷酷無情的人。
“接著我告訴她,希姆萊被埋在一處無名墳墓中,”斯特林格繼續(xù)記述道,“希姆萊女士既未流露訝異表情,對此似乎也不感興趣。她以冰冷而決絕的方式展現(xiàn)出一種對人類情感的自我控制,那是我從未見過的情景……然后我問她是否意識到世人對她丈夫的觀感。她的回答是:‘我知道大戰(zhàn)以前很多人非常景仰他。’瑪嘉知道丈夫被視為頭號戰(zhàn)犯時,倒顯得相當錯愕:‘我先生?這怎么可能?希特勒才是帝國大統(tǒng)領呀!’”*后,斯特林格提到數(shù)以百萬計的無辜者因為酷刑虐待、饑餓、寒冷、生病而死,甚至被大批送進毒氣室,然后她問瑪格麗特對這一切是否感到驕傲,瑪格麗特說:“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這得看情形。”這樣一個女人完全無法引起他人同情。
1945年9月26日,瑪嘉·希姆萊在紐倫堡接受訊問時宣稱,跟許多納粹要員一樣,海因里希·希姆萊遵守組織的要求,身上隨時備有毒藥。瑪嘉還證言,她會跟丈夫討論戰(zhàn)情,但她否認曾跟他談到集中營的事。“我從來不知道這件事,我是現(xiàn)在才知道的。”在紐倫堡負責偵訊的美軍上校艾門(Amen)問她:“為什么你從來不曾針對這個話題詢問他?”她回答:“我不知道。”但當她被問到這個問題:“你知道他在不同地方成立集中營,沒錯吧?”她聲言道:“對,我知道有一些集中營存在,但我不知道是誰告訴我的。我記不得了,有可能是他吧,我只知道他們蓋了一些集中營。”瑪嘉起初否認集中營的事,后來終于承認這項業(yè)務是由她的丈夫所負責,并坦言她曾親自前往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參觀設在那里的女子集中營。盡管如此,她還是表示自己對那里面發(fā)生的事一無所知,要等到1945年,她才通過報刊媒體得知這一切。
歌德倫一直到1945年8月20日,在一名美國記者采訪她母親時,才不期然地聽說她父親在接受偵訊以前就已經(jīng)服毒自盡。少女震驚過度,結果生了一場大病。她發(fā)高燒,神志不清地在羈押營的野戰(zhàn)床上躺了三個星期。她相信父親是被盟軍謀殺的,他絕不可能自行了斷。負責看管她的英國指揮官這時一心只有一個念頭:趕快把這個麻煩孩子甩掉。誰也不想背負“希姆萊之女”這個累贅,她對同盟國毫無用處,而且保護她是非常艱巨的任務。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給她換個姓氏。于是她開始姓“施密特”,不過為時并不久。
1946年11月以前,在除納粹化審判期間,希姆萊的妻女被羈押在路德維克斯堡(Ludwigsbourg)的七十七號女子拘留營。拘留營指揮官決定釋放她們時,瑪格麗特拒絕離開,因為她身無分文,害怕遭到私刑,而且也不知道能到哪里去。*后她們被“大馬士革之家”收容,那是博德爾施文格(Bodelschwingh)牧師創(chuàng)設的一家基督新教修道院兼救濟院,母女兩人以“智能不足”的名義登記入院。修女們設法跟歌德倫交流,但她一直保持距離,而且不斷強調(diào):“我要跟我爸爸一樣。”也就是說要當個天主教徒。的確,希姆萊年輕時是個極為虔誠的天主教徒,雖然他后來遠離了教會,但每天晚上仍舊會跟女兒一塊禱告。修女們從沒看過這名少女哭或笑。1952年,歌德倫和母親離開了這座修道院。
在二十歲的年紀,我們對周遭的事物有什么樣的意識?歌德倫從不保留、毫不退縮地喜愛父親,父親對她則疼愛有加;而且他自始至終一直堅信自己是個服膺“道德”的人。只有一個因素能讓那些人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符合道德:納粹思想。納粹主義認為人類間存在著絕對的不平等,并以此為核心概念,建構出一套獨有觀點。這種思想使納粹主義者完全罔顧普世性的道德。但當歌德倫終于發(fā)現(xiàn)父親犯下殘酷罪行時,她已經(jīng)不能再拿第三帝國的獨特道德觀當借口了。
1947年間,歌德倫嘗試進入一所應用藝術學院就讀,但校長看到她的姓氏以后,立刻拒絕了她的入學申請。當她被問到她父親的工作時,她會面不改色地回道:“我的父親是黨衛(wèi)軍帝國統(tǒng)領。”不過在比勒費爾德(Bielefeld)社會民主黨主任的介入說情之后,她終于在第二個學期順利注冊就學。這名主任認為懲罰不可以施加于一整家的人:“我國的年輕民主制度不容許讓兒童因為父母犯的錯而受苦受難。”歌德倫開始修習裁縫訓練課程,然后到一位服裝設計師那里當學徒。1950年代,她離開母親,前往慕尼黑居住,設法在那里找工作。這時她的年紀是二十一歲。后來她得知同父異母弟妹的下落,設法跟他們?nèi)〉寐?lián)系,但沒有成功;希姆萊的情婦赫德薇格·波特哈斯特反對這件事。世人對這名希姆萊情婦在大戰(zhàn)結束以后的生活所知甚少。1950年代,她離開巴伐利亞,遷居到黑森林地區(qū)巴登巴登附近的一座村莊。她住在一名女性友人家附近,那人名叫喜古德·派培(Sigurd Peiper),她曾經(jīng)在黨衛(wèi)軍帝國首領希姆萊的個人幕僚處擔任秘書,她的丈夫因為戰(zhàn)爭罪被判刑入獄。后來赫德薇格再婚,姓氏也隨之更改。關于她的小孩,我們幾乎一無所知,他們生活在近乎完全匿名的狀態(tài)中。我們只知道希姆萊跟情婦生下的兒子因為健康問題的關系,一直留在母親身邊,他們的女兒則成了一名醫(yī)生。1994年,赫德薇格·波特哈斯特在巴登巴登去世。
每當歌德倫說出她的姓氏——“希姆萊”,她立刻就會遭到制裁:不是被轟走,就是被趕出租住處。然而,她卻執(zhí)意保有父親的姓氏。她的工作同僚、她在各家公司接觸到的客戶,這些人都拒絕跟她來往,他們不愿意讓一個姓“希姆萊”的人提供服務。
1955年,她跟希特勒時代德國外交部部長的兒子阿道夫·馮·里賓特洛甫(Adolf von Ribbentrop)聯(lián)袂前往倫敦,參加奧斯瓦德·莫斯里舉辦的一場宴會。返回德國以后,她相當驕傲地表示她在倫敦見到許多法西斯主義者。這件事傳開以后,她立刻被她任職的特格爾恩湖畔旅棧解雇。一名客人得知前臺女服務員是海因里希·希姆勒的女兒以后,嚴詞抗議道:“我太太在奧斯維辛的火爐里被烤成灰炭,你們怎么可以讓這個女的接待我?”歌德倫在慕尼黑郊區(qū)格奧爾根街的小公寓儼然是一座為父親歌功頌德的博物館,里面擺滿畫作、擺設、裝飾品、塑像、照片等,都是她從幼年時代開始不斷收集的物品。她也會到歐洲各地搜羅文物,有時還得到一些前納粹黨員的協(xié)助,他們也保存了一些相關遺物。后來她成為一名秘書,過著簡單的生活,把自己奉獻給她那慈愛的父親。她一直無法想象父親曾經(jīng)竭力參與人類歷史上*殘酷的戰(zhàn)爭罪行之一。她不斷想要捍衛(wèi)他。一方面她對父親充滿孝心和感念,另一方面卻又不免知道父親是個納粹狂熱分子、黨衛(wèi)軍猛獸,主導、執(zhí)行了慘絕人寰的*終解決方案。兩相糾結,她感到無所適從。但她在內(nèi)心相信,總有一天會有新的事證能為父親洗清罪名。擺在她面前的證據(jù)無可辯駁,但這些都不足以說服她。她跟父親之間獨特而緊密的聯(lián)結是否可以用來解釋她為何如此盲目?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很難得到確定的答案,因為她一直拒絕表態(tài)。終其一生,她只真正接受過一次媒體訪問,那是1959年的事,采訪人是德國記者諾爾貝特·雷貝特(Norbert Lebert)。
多年以后,雷貝特的兒子斯特凡在他的著作《因為你承載了我的名》中援引了他父親的采訪資料。他在書中強調(diào),像歌德倫這些歌頌父親光榮過往的納粹小孩其實從這種崇拜行為中取得了一部分的自信。這些小孩無法承認他們的家庭背景所造成的沉重負擔。歌德倫只從父親身上看到一家之主的慈愛形象,父親人格的另外那個面向都是媒體和書籍告訴她的。對某些納粹后代而言,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否定外在于他們自身經(jīng)驗的一切資訊,無論那些資訊多么合理切實。任何其他辦法都會構成一種背叛。此外,歌德倫終其一生都必須面對被人排斥的處境,這可能也導致她認為自己是社會不公的受害者,因此父親的命運等于是在她身上延續(xù)。
1951年起,歌德倫成為“戰(zhàn)犯及被囚禁者無聲協(xié)助協(xié)會”(Stille Hilfe für Kriegsgefangene und Internierte)的成員。起初該協(xié)會的會長是海倫妮·伊莉莎白·馮·伊森伯格(Helene Elisabeth von Isenburg)親王夫人,她是個長袖善舞的名媛,在上流布爾喬亞社會及教會中交游廣闊。這個機構支持的罪犯由魯?shù)婪颉ぐ⑸徼?Rudolf Aschenauer)律師提供法律支援。根據(jù)馮·伊森伯格親王夫人所言,協(xié)會宗旨是對該機構認為遭到褫奪所有權利的戰(zhàn)犯及被囚禁者提供服務,滿足他們的各種需求。在戰(zhàn)后的相關司法訴訟中,該機構也支持被告及被羈押者,無論他們是被監(jiān)禁在戰(zhàn)勝國的監(jiān)獄還是德國的服刑所。親王夫人喜歡將自己比擬為被關押在巴伐利亞蘭茨貝格(Landsberg)美國監(jiān)獄那些納粹罪犯的母親。1924年,希特勒也曾在這里被關了九個月,其間寫成《我的奮斗》。
1952年,歌德倫又協(xié)助創(chuàng)辦“維京青年團”(WikingJugend)。這個運作模式仿效“希特勒青年團”的組織在1994年被德國禁止。
“無聲協(xié)助協(xié)會”的核心分子包括二十名到四十名會員及一百余名支持贊助人士。協(xié)會也為逃犯提供支持。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約翰·馮·萊斯(Johann von Leers)、約瑟夫·門格勒等人都受益于這個納粹滲透網(wǎng)絡——同盟國所稱的“老鼠線路”(rat line)。通過“無聲協(xié)助”會員孜孜不倦的支援,這些人都順利逃到拉丁美洲。被稱為“里昂屠夫”的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也得到該組織的幫助。《默默協(xié)助褐衫伙伴們》(Stille Hilfe für braune Kamaraden)一書作者安德烈亞·羅普克(Andrea Rpke)及奧利弗·施洛姆(Oliver Schrm)指出,“無聲協(xié)助協(xié)會”不僅支援前國社黨黨員,也在臺面下籌募資金,支持新納粹運動。
陸續(xù)有記者試圖針對這點向歌德倫·希姆萊提問,但她只給一個簡短的答復:“我從來不談我的工作,我只是在我可以的時候做我能做的事。”在她的相關活動中,她特別介入?yún)f(xié)助了安東·馬洛特(Anton Malloth),這個人物是特雷辛城集中營的黨衛(wèi)軍高級隊長,他是*殘酷、*令人聞之色變的監(jiān)管人員之一,想必也是歌德倫父親的心腹。大戰(zhàn)結束以后,馬洛特在意大利的梅拉諾無憂無慮地生活了四十年。1988年,他被引渡到德國。由于某些程序問題,他一直到2001年才被慕尼黑法院定罪,判處無期徒刑。在那些年間,歌德倫·希姆萊一直是他的主要支持者。“無聲協(xié)助”幫他在一所高級養(yǎng)老院找到住處,那座養(yǎng)老院就建在一塊于第三帝國時代由希特勒副手魯?shù)婪颉ず账钩钟械耐恋厣稀?990年,消息指出德國社會保險局支付了馬洛特在那里生活的大部分費用,也就是說,德國納稅人掏錢讓一名兇殘戰(zhàn)犯樂享天年。結果撻伐之聲四起,特別是歌德倫·希姆萊受到嚴厲指控。但歌德倫忠誠不變、心意堅定,每個月都會前去探視他兩次,直到他在2002年死去為止。
如果歌德倫決定大隱于世,那是因為對于她的家庭背景,她所持的立場不見容于社會。她積極投效各個為前納粹分子提供援助的機構,并公然支持德國極右派,這些都表明她不只是希望平反父親的名聲,也想要承繼他的黑暗理想。
1960年代,歌德倫跟一名親納粹分子結婚,丈夫名叫沃爾夫迪特·布爾維茨(WolfDieter Burwitz),他是一名作家,并在巴伐利亞政府擔任公務員。他接受了妻子的家庭背景,并認同她父親的理想。夫妻兩人生活在慕尼黑郊區(qū)福斯滕里德(Fürstenried)的一棟白色大宅中,育有兩名兒女,兒子長大后在慕尼黑擔任財稅律師。
2010年,“無聲協(xié)助”試圖阻止荷蘭籍納粹分子克拉斯·卡雷爾·法貝爾被遣送回國。荷蘭法院在1947年將他定罪判刑,罪名是在大戰(zhàn)期間殺害二十二名猶太人和反抗軍成員。
歌德倫據(jù)稱也是極右派德國國家民主黨(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NPD)的活躍分子。她似乎不喜歡受到褒揚,例如在奧地利北部烏爾里希斯貝格(Ulrichsberg)舉行的納粹集會這類場合,她的言行都非常低調(diào)。或許她會想到,無論她怎么做,一切都會將她拋回那個縈繞不去的過往?在這種情況下,否認那個過往完全無法消解她的宿命。或許跟她的父親一樣,她選擇放棄道德良知,不直接面對那個重擔。有沒有可能希姆萊的“小娃娃”真的從未受罪惡感折磨,而她的侄孫女卡特琳卻表示自己“經(jīng)常感受到一種無從解釋、令人心情沉重的自責”?這種自責感有時會隔代傳承。卡特琳·希姆萊的丈夫是二戰(zhàn)期間華沙猶太人居住區(qū)一個猶太家庭的后代,在她成為母親時,她決定詳細回顧家族歷史,寫成《希姆萊兄弟》一書。她在求學時期得知納粹犯下的殘酷罪行,但跟許多德國人一樣,她在很長時間中無法真正審視自己的家族背景。她指出,如果問題涉及非常親近的人,內(nèi)心的防御機制會太強:“那是一個極為艱辛的過程,害怕被遺棄的焦慮感不斷構成威脅。”考慮到自己跟歌德倫·希姆萊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她完全沒跟這位堂伯母聯(lián)絡。
在當事人是納粹子女的情況下,這種防御機制會特別頑強。在這方面,歌德倫·希姆萊的特點是她完全無法退一步思考她父親這個人物所代表的意義,并且持續(xù)在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殘存勢力中扮演積極角色。對她而言,緬懷父親跟服膺及提倡納粹思想是同一回事。
羅爾夫·門格勒:“死亡天使”之子
2011年7月21日,設于美國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專營歷史手稿買賣的亞歷山大真跡公司(Alexander Autographs)舉行拍賣會,現(xiàn)場第四組拍賣品的說明文字寫著:“內(nèi)容完整的檔案資料,可供深入審視二十世紀*殘忍人物的心理樣貌。所有內(nèi)容均經(jīng)詳細閱讀與分析,絕大多數(shù)未曾出版,甚至不曾有人閱覽。”
成交,售出!拍賣官槌子落下的聲音敲響廳堂。一名極端正統(tǒng)派猶太人通過電話出價,以二十四萬五千美元價格買下三千三百八十多頁以藍色墨水寫成的手稿。買主是一名大屠殺幸存者的兒子,他不希望公開身份。他認為這樣的文件一定要讓民眾看到,借以對抗所有可能導致歧視的否定論及教條。
這組文稿包括三十一本黑色、卡其色、綠色或方格設計螺旋裝訂學生筆記本,封面上分別以西班牙文印有Cuaderno(“筆記簿”)、Cultura General(“文化素養(yǎng)”)、Agenda Classica(“古典教程”)等標注。內(nèi)頁上寫滿文字,工整的筆跡棱角分明,略朝右邊傾斜。圖畫及速寫穿插在自傳式書寫、詩作、政治及哲學思考評述之間。這些手稿是在1960—1975年撰寫而成。
這筆拍賣引發(fā)熱議。有些評論家認為這種文件不應該成為商業(yè)行為的標的,甚至批評這是一件“淫穢”的銷售案。
這些文字的作者以第三人稱敘述自己的故事,并采用筆名“安德烈亞斯”。這個人物是二十世紀*受矚目的逃犯之一,他隱身在化名后方,生怕這些筆記本有朝一日會惹禍上身,讓他行跡敗露。他在筆記中回溯他在戰(zhàn)后跨越歐洲大陸、逃向拉丁美洲的過程;跨海前往阿根廷、巴拉圭,*后抵達巴西。他也描述了他做過的各種實驗,他認為那些實驗結果對人類福祉有貢獻。
在他的文字中,作者完全不否定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并且致力闡述他在人口過剩、優(yōu)生學、安樂死等方面的理論。
他在1960—1962年特別提到:“一旦我們開始混合不同民族,文明就會式微。”①他又說:“自然界中沒有好也沒有壞,只有適當?shù)脑睾筒贿m當?shù)脑亍贿m當?shù)脑乇仨毐慌懦诜敝吵绦蛑狻!彼€說:“我們必須揚棄女性主義思想;生物學與權利平等毫無關聯(lián)……女性不應該掌管需要專業(yè)資格的職務。女性的勞動參與必須取決于她們有多少能力滿足她們的生物配額。生育控制必須通過絕育方式進行,有基因缺陷的女性必須予以結扎。基因良好的女性則應在生育五名子女以后才予絕育。”
這些筆記本于2004年在巴西圣保羅的一對男女住處被查獲,他們在此之前曾經(jīng)為這些文字的作者提供住宿。筆記本后來被轉交給作者的唯一親生子——羅爾夫。羅爾夫就是這些筆記的賣家嗎?沒有人知道,因為在那場拍賣中,賣家也不希望身份曝光。
日復一日,約瑟夫·門格勒都會坐在他的小桌前,重新觀照他的光輝年代,以及那些仿佛永無止境的逃亡時日。在歲月的層層重壓下,門格勒的身形已經(jīng)逐漸蜷曲。十五年以前,他開始撰寫這些筆記。此后他的信念從未改變,經(jīng)過三十四年的潛逃,他仍然堅守原來的想法,直到*后一刻。他不但深信自己沒犯過任何錯,他的流亡生涯更使他成為書寫偏執(zhí)狂。他幽閉在圣保羅郊區(qū)的小房子中,將大部分時間用于寫作。他在筆記本紙頁上描繪他的巴伐利亞風格家具,畫出一幅幅房屋、動物及植物的速寫圖案。他也勤于園藝、木工,熱愛健行,喜歡觀賞動植物。
1977年,他等待多年的一天終于到來:他的獨生子從歐洲過來拜訪他。他已經(jīng)二十一年沒跟兒子見面了;*后一次看到他還是1956年的事。當時他的兒子并不知道這個使用偽造身份的人就是他的父親。因此,父子兩人是今天才真正相認,而且這是一場充滿風險的會面,因為惡名傳四海的約瑟夫·門格勒醫(yī)師是地表*重要的通緝犯之一。他被冠上“死亡天使”的綽號,因為他在奧斯維辛做過無數(shù)駭人實驗。
為了避免兒子的行蹤被納粹緝捕者發(fā)現(xiàn),這趟旅行花了整整五年時間籌備。羅爾夫·門格勒動身前往巴西前,門格勒家的親信漢斯·賽德爾梅耶(Hans Sedlmeier)安排羅爾夫和他的堂親卡爾海恩茨(Karl Heinz)見面,這位堂親先前在阿根廷跟約瑟夫·門格勒一起住過幾年。賽德爾梅耶希望羅爾夫留意一個問題:年輕一代德國人對第三帝國的理解跟親身經(jīng)歷過那個年代的人的內(nèi)心感受有極大落差。他也打算轉交一筆錢給門格勒——門格勒的親人向來為他提供堅不可摧的支持。
羅爾夫聽從父親的建議,以匿名方式前往圣保羅,為此他事先特地在跟一名朋友一起度假時,盜取了他的護照。他決心要跟父親重逢,盡管他表示自己已經(jīng)不再像小時候那樣認為父親是個英雄。他認為自己跟父親毫無共通之處。“我的見解跟他完全相左。我連聽他說話都不想,對他的看法也完全沒興趣。我完全排斥他告訴我的一切。我對國家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個人立場再清楚不過,所有人都知道我的政治理念屬于自由派,基本上偏向左派。歷年來我發(fā)表過的許多批判甚至讓人懷疑我是共產(chǎn)黨。”
夜幕低垂之際,一輛老舊公交車開進圣保羅郊區(qū)這條塵土飛揚的街道,疲憊的老人一陣心驚,四肢開始顫抖。骨骼突出的雙手嵌進舊長褲口袋,他板著臉孔,動也不動地等著。過去的他非常講究穿著,現(xiàn)在他對自己的外表毫不在乎。他知道他的兒子這天晚上會到,但他不禁想到來者也可能是準備逮捕他的納粹追獵者。即使在他的悲慘人生走向盡頭之際,門格勒依然從不降低警戒。從前那個宰制奧斯維辛集中營、精于算計的冷酷男子已然遠去,在長年的逃亡生活中,他早已成了個被恐懼啃噬的老頭。他像偏執(zhí)狂般地害怕自己被搜捕。這種恐懼比任何感覺都強烈,將他整個人吞沒。焦慮使他不由自主地吸吮、啃食自己的胡須,經(jīng)年累月下來,毛發(fā)在他肚子里形成球狀物,堵塞他的消化道,使他痛苦難當,甚至連生命都受到威脅。
許多年來,門格勒獨自一人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他住的黃色灰泥小屋非常簡陋,里面只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一張床和一個櫥柜。房子的傾斜屋頂和兩扇白色窗戶,以及四周的幾棵大樹,使它稍微流露出阿爾卑斯小山莊的氣息。
他的兒子走過庭院木門時,他難掩激動之情,淚水涌上眼眶。雖然他的腿難以支撐他,但他還是設法走到門口臺階上,歡迎突破艱難險阻前來看他的兒子。如同羅爾夫所言,他的父親認為他敢到巴西看他,就足以證明他是個大膽跨越敵軍防線的英勇士兵。但情況并非一直如此。
這天,羅爾夫成了父親心目中的英雄。為了見這個過去從來不屑對他表示興趣的人,他冒了許多風險。在他的童年時代,他的父親忙于犯下殘暴得無以復加的罪孽,等他年齡稍長,父親又忙著逃脫盟軍及納粹追獵者。他花在這個孩子身上的時間少之又少,只有一些往返書信勉強撐出某種親情關系。
羅爾夫想要親眼看到父親,但跟他面對面時,他發(fā)現(xiàn)自己幾乎認不得這個他至今只短暫見過兩次的人。他非常驚訝地看到這個偽裝高手身體變得如此瘦弱。他也知道這次會面對他的父親而言是件天大的事。羅爾夫冒險犯難跨海而來,是為了像個檢察官般審問這個三十多年來一直成功躲過同盟國法庭制裁的逃犯嗎?不,他要的是設法理解。理解這個無論如何都是他父親的人何以能如此瘋狂地投入那部恐怖死亡機器的運作。
曾經(jīng)長期被門格勒家族視為害群之馬的他目前是一名在德國弗萊堡執(zhí)業(yè)的律師。他的親屬認為他是個極端派左翼分子,他向來認為自己跟家人除了血緣之外沒有其他任何共同點,而那個血緣非同小可,源自全世界*受憎恨的人——他的父親。羅爾夫作這趟旅行時是三十三歲,他的父親在同樣年紀時,在奧斯維辛擔任醫(yī)生,只要做個手勢,就能決定成千上萬的人是生還是死。
沒有任何幸免于難的人能夠忘記這個人的模樣,他擁有地中海地區(qū)人民的長相,舉止高雅,身穿無懈可擊的軍服,皮靴擦得烏黑油亮,手里總是握著一根短馬鞭。他用手指輕輕一點,就選定接下來的實驗對象:往右是他的實驗室,可以暫時活命;往左則是死。他把無數(shù)男女老幼趕向毒氣室或陰森可怖的實驗室時,臉上沒有顯露任何表情。他喜歡哼唱瓦格納或普契尼的曲調(diào),人們哪里知道美妙樂音出自一個位居死亡機器核心的人物。
羅爾夫只能輕聲說了句“爸,好”。兩個人的短暫相擁顯得相當冷淡,他們都不習慣流露情感。羅爾夫強迫自己表現(xiàn)得親切熱誠,畢竟他都說過“他終究是我的爸爸”;但他難以真正做到這點,直到他感覺父親的淚水沿著臉頰流下。
這是門格勒開始逃亡以后兒子羅爾夫第二次見到他;這也將是*后一次。**次跟他見面時,他的母親告訴他說,他會見到一位住在拉丁美洲的“弗里茨伯伯”。多年以后,他才知道原來那位伯伯是他的父親,然后了解到這個父親在德國那段晦暗歷史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羅爾夫糾結在兩種情緒中:身為人子,他對父親有敬愛之情,但想到那些泯滅天良的罪孽,他又無法遏制地唾棄他。對絕大多數(shù)世人而言,約瑟夫·門格勒是一名戰(zhàn)爭罪犯,但在門格勒家族成員的心目中,他依然是個值得嘉許的杰出醫(yī)生。從家族的立場來看,*要緊的事是絕不可玷污家姓:他們可是巴伐利亞的產(chǎn)業(yè)界望族,而以老大約瑟夫為首的三兄弟有責任傳承家風。
專營農(nóng)業(yè)機具制造的“卡爾·門格勒父子公司”是巴伐利亞君茨堡(Günzburg)市的主要雇傭單位之一。由于這家公司鼎力支持國家社會主義,它在第三帝國期間成為德國農(nóng)業(yè)機具制造界的第三大企業(yè)。希特勒曾經(jīng)親自蒞臨發(fā)表演說。“卡爾·門格勒父子公司”至今依然存在,公司名稱以斗大字體標示在位于市區(qū)中央的工廠上方。有一條街道甚至以約瑟夫的父親卡爾·門格勒命名。但在君茨堡,我們卻找不到任何與那個令人困擾的兒子有關的痕跡。
農(nóng)業(yè)機具從不曾引起老大約瑟夫的興趣,他寧可把公司繼承權讓給兩個弟弟。在校表現(xiàn)非常優(yōu)秀的約瑟夫從小就滿腔抱負、熱血激昂,他的*大心愿是在歷史上聲名永傳。
1930年,他在慕尼黑修讀哲學、人類學與醫(yī)學時,納粹的理想已經(jīng)充斥在德國各地的大學校園中。他很快就開始向一些深信優(yōu)生學的學者“拜師習藝”,對恩斯特·魯丁(Ernst Rüdin)的講座尤其熱衷。魯丁是納粹德國的優(yōu)生學泰斗,在他的背書下,德國通過了對患有遺傳缺陷的人民實施絕育的法律。1935年,在慕尼黑大學“種族衛(wèi)生”專家提奧多·摩里森(Theodor Mollison)教授指導下,約瑟夫·門格勒完成了一篇內(nèi)容充滿優(yōu)生學理論的博士論文,標題為《針對四個種族群體所作之下腭前端形態(tài)學檢驗》。當時門格勒就已經(jīng)相信有一種優(yōu)越種族的存在,也就是“雅利安型德意志人”,而他打算用科學方法加以證明。
門格勒在慕尼黑大學期間成為優(yōu)生學家、種族純凈暨衛(wèi)生研究院院長及納粹優(yōu)生學政策煽動者奧特馬爾·馮·費許爾(Otmar von Verschuer)的助理,畢業(yè)后又于1938年轉往法蘭克福大學深造。馮·費許爾教授相信,金發(fā)碧眼的純粹雅利安種族典范的關鍵存在于雙胞胎的專屬基因中。1937年,門格勒加入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即通稱的納粹黨),黨員編號5574974,然后他又在1938年加入黨衛(wèi)軍。為了證明他的血統(tǒng)純粹,他積極調(diào)查自己的“種族純凈度”,一路回溯到1744年。
門格勒深信德國的未來維系在基因操縱上。通過他對雙胞胎的研究,他野心勃勃地希望讓德意志民族大量繁衍。他跟馮·費許爾教授一起試圖判定哪些基因密碼可以催生出純凈的雅利安種族。國家社會主義需要為它所支持的種族衛(wèi)生理論找到科學上的立論基礎,因此門格勒積極投入這方面的研究。
1939年,約瑟夫·門格勒與羅爾夫的母親伊雷妮·舍恩拜因(Irene Schoenbein)結婚。起初由于伊雷妮難以證明她父親家那邊沒有猶太血統(tǒng),結婚手續(xù)卡在這個問題上無法過關,一時之間,他們無法取得結婚許可。后來因為伊雷妮的“明顯北歐長相”化解了上述疑慮,兩人才得以順利成婚。伊雷妮這個高挑的金發(fā)美女成為約瑟夫的一生摯愛,她自己則是個非常賢惠的妻子,但非常容易嫉妒。羅爾夫的父母一直無法好好過夫妻生活。對伊雷妮而言,這場婚姻帶來的經(jīng)常是獨守空閨的苦悶,因為門格勒把生活重心完全放在專業(yè)生涯及愛國行動這個部分。結婚短短兩個月后,德國入侵波蘭,門格勒立刻斗志昂揚地參軍,縱使將年輕妻子獨自留在家鄉(xiāng)也無怨無悔。
1942年,他加入黨衛(wèi)軍“維京”裝甲師醫(yī)療團,這支部隊的行動范圍是東方戰(zhàn)線,特別是烏克蘭。參軍期間,門格勒因為救援并醫(yī)治兩名德國士兵,獲頒鐵十字勛章。后來他在戰(zhàn)斗中受了傷,被迫提前退役,于1942年底返回柏林。他毫不猶豫地重新投入醫(yī)學工作,尤其是在基因遺傳領域,而他追隨的老師依然是馮·費許爾教授。門格勒從軍那段時間,馮·費許爾成為“威廉皇帝研究院”院長,這個科學機構的成立宗旨是基礎科學研究,但在1927—1945年,研究重點是優(yōu)生學及種族衛(wèi)生。
四個多月后,約瑟夫·門格勒于1943年4月被任命為黨衛(wèi)軍高級突擊隊領袖。5月底,他被派到奧斯維辛集中營。這是納粹政權成立的**大集中營,位于克拉科夫以西六十七公里,接近捷克斯洛伐克邊界。
奧斯維辛當時儼然已經(jīng)是一部毫不留情的產(chǎn)業(yè)化滅絕機器。四個大型毒氣室及焚化爐作業(yè)區(qū)不停運作,煙霧從那里不斷冒出,使空氣令人難以呼吸。天氣炎熱時,人肉的味道更是讓人窒息。集中營占地遼闊,包含三個大區(qū),而且不斷逐年擴大,一模一樣的紅磚及木造營舍持續(xù)往外擴展。門格勒對這個人間地獄般的景象絲毫不為所動,他一到奧斯維辛,就馬不停蹄地前往十號營舍。
他要立刻投入工作。對他而言,奧斯維辛是個有助于促進科學進步的獨特場所,提供了針對“人體白老鼠”進行實驗的絕佳機會,讓他能證明他的種族理論觀點。門格勒經(jīng)常會將標有“戰(zhàn)爭材料,速辦”這句話的人體碎塊寄回威廉皇帝研究院,供同儕分析研究。
門格勒抵達幾天以后,就毫不遲疑地將一千五百名吉卜賽人處死。諷刺的是,他經(jīng)常自嘲長得比較像吉卜賽人,而不像完美的雅利安人。小時候,由于膚色偏深、頭發(fā)全黑,而且眼睛呈褐色與棕色,他曾經(jīng)因此在學校被取了“吉卜賽”這個綽號。
門格勒只身前往奧斯維辛。他的妻子選擇留在德國。在他待在集中營的一年半期間,妻子只去看過他兩次,**次是1943年8月,然后是1944年8月,也就是在羅爾夫出生幾個月以后。羅爾夫是在3月出生,伊雷妮前往奧斯維辛時將他留在德國。她問丈夫為什么營區(qū)中有那么可怕的味道,丈夫只給了這個回答:“別問我這件事。”不過伊雷妮似乎也不是很關心周邊發(fā)生的事。她甚至覺得第二趟旅行非常浪漫,仿佛是在跟她心愛的男人度第二次蜜月。白天他們會到索拉河游泳,還有采藍莓做果醬。在她的日記中,沒有一句話提到她丈夫所做的實驗或集中營的實際情況。門格勒是個冷酷無情、憤世嫉俗而且深藏不露的人,很少跟同僚打成一片。他對自己的地位和他拿到的各種獎章非常自豪,身上總是佩戴著那個鐵十字勛章。他的生活跟其他人沒什么交集,一心一意地專注在他為自己定義的使命——改善人類的演化,即使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必須置人性或憐憫于不顧。
門格勒的職務令某些同僚深感好奇,例如他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工作伙伴漢斯·蒙希(Hans Münch)。“他從身體到精神整個都是意識形態(tài)的化身……他從不表現(xiàn)出任何情感;既沒有仇恨,也沒有狂熱,”蒙希曾表示,“對他而言,毒氣室是唯一合理的解決方案,而由于猶太人無論如何都得死,他認為理所當然應該事先用毒氣室來做一些醫(yī)學實驗。”⑩所有人對門格勒醫(yī)師都一無所知。他那種城府很深的保留態(tài)度使他跟其他人之間自然而然就拉開距離。1944年兒子羅爾夫出世時,他沒告訴任何人;此外,妻子生產(chǎn)時,他也沒有前去探視她。
起初小羅爾夫跟母親一起住在黑森林地區(qū)的弗萊堡。1944年11月,約瑟夫·門格勒才**次去看兒子,這時兒子已經(jīng)將近八個月大。1945年4月起,伊雷妮帶著羅爾夫遷居到巴伐利亞的奧滕里德(Auteried),那里距離門格勒家族的地盤很近。于是小羅爾夫開始能跟祖父母朝夕相處,終于過起真正的家庭生活。
來自歐洲各地城市的火車不斷開進奧斯維辛。新到的人必須經(jīng)過一道預先篩選程序:被視為身強體壯的人會被送去強制勞動,其他人則直接被送進偽裝成淋浴間的毒氣室。不分晝夜,每當有火車抵達,門格勒都會守候在那里抓雙胞胎,用他們做各種殘酷實驗,而這些實驗通常會導致他們在恐怖的痛苦中死亡。通過這些與雙胞胎現(xiàn)象有關的實驗,他相信自己一定能破解基因遺傳的秘密,全面根除有缺陷的基因。于是,當雙胞胎出現(xiàn)在篩選過程中,他聽到有人大聲喊“雙胞胎,雙胞胎”時,他平日陰沉的臉孔就會驟然明亮起來。
他做了無數(shù)的實驗,而且都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進行:操縱血液、接種感染基因、骨髓實驗、器官割除、截肢、結扎。約瑟夫·門格勒也對眼睛的顏色深感興趣,他想知道是否能改變?nèi)说难劬︻伾榱诉_到這個目的,他會給他的“病人”注射化學物,結果大都造成他們失去視力。這些實驗的唯一目標是:弘揚一個符合國家社會主義理想的優(yōu)越種族。
1945年1月17日,門格勒逃離奧斯維辛時,他在身后留下堆積如山的尸體。他的“人類白老鼠”幾乎都不可能在他的恐怖實驗結束以后存活,不過根據(jù)一名幸存者的說法,被門格勒排入實驗名單至少能在短時間內(nèi)帶來生存的希望。納粹政權解體時,大批落敗德軍往西方潰逃,使他借機躲過盟軍的搜捕。他把黨衛(wèi)軍制服換成國防軍制服,然后躲避在捷克斯洛伐克地區(qū)。由于逃亡德軍如排山倒海而至,盟軍無暇應付,決定只抓黨衛(wèi)軍,而黨衛(wèi)軍成員的特征是在手臂內(nèi)側有個人血型的刺青。不過,因為門格勒非常注重維護自己的身體,他拒絕像其他黨衛(wèi)軍成員那樣在手臂上留下刺青。這個個人堅持救了他一命,因為當時盟軍沒有完整的戰(zhàn)犯名單。羅爾夫的母親告訴過他,他的父親極為注重外表,因此他認為絕不可以讓身體遭受那種殘害。門格勒只穿量身定做的高級西服,平日喜歡站在鏡子前面觀賞自己的英姿、贊嘆自己的細柔肌膚,對這樣一個人而言,黨衛(wèi)軍的血型刺青不僅不好看,而且令人極度反感。
伊雷妮很久沒有丈夫的消息。大戰(zhàn)結束后不久,一名醫(yī)界朋友的妻子忽然通知她說門格勒安然無恙。不過他的名字已經(jīng)開始流傳,盟軍密切注意任何可能有助于將他逮捕的消息。這名逃犯的所有家族成員都受到監(jiān)視和訊問,但沒有具體結果;他們都不愿提供任何訊息。德國《聯(lián)邦報》(Bund)曾經(jīng)刊登評論,指出門格勒家族對他提供堅實的支持,因為他們害怕約瑟夫·門格勒的被害者可能對他們提出賠償訴訟。
伊雷妮接受兩名搜尋她丈夫的美國軍官訊問時告訴他們,門格勒已經(jīng)消失無蹤,很可能在東歐前線戰(zhàn)死了。為了替這個假設提供可信度,平日總是一身黑色裝束的伊雷妮特地在1946年夏天去找了君茨堡的神甫,請他幫忙作彌撒悼念她為國捐軀的丈夫。門格勒夫人雖然曾經(jīng)造訪過奧斯維辛集中營兩次,但她在相當長的時間中并不知道丈夫犯下的殘暴罪行,不過到了這個時候,她已經(jīng)不可能不知道,只是她選擇不要譴責他。
門格勒在慕尼黑短暫停留以后,回到他的家鄉(xiāng)君茨堡,躲在附近的森林中,他的家人經(jīng)常會供應食物給他。當局完全沒察覺到這件事,就連一份以色列警方的報告也沒提到門格勒跟他的家人之間有任何接觸。
1945年底開始,“死亡天使”用“弗里茨·霍爾曼”(Fritz Hollman)的化名低調(diào)過活,在巴伐利亞羅森海姆(Rosenheim)當農(nóng)工(后來他以“美洲伯伯”的身份見到兒子時,用的也是這個假造的名字)。他的家人——特別是他的妻子——經(jīng)常到農(nóng)場看他,有時妻子也會把當時才兩歲的小羅爾夫一起帶去。他們會小心翼翼地在一個湖邊見面。在那段時間拍的一張照片上,可以看到滿臉笑容的門格勒站在兒子身后。不過多數(shù)時候伊雷妮是單獨赴約。1946年11月,門格勒認為盟軍已經(jīng)松懈調(diào)查腳步,于是他壯起膽子前往奧滕里德看望當時已經(jīng)搬到那里的妻兒,一待就是兩星期。
羅爾夫表示,在大戰(zhàn)結束以后那四年,他的母親非常焦慮而且不快樂。她的心愿一直是能夠在一個關系緊密的家庭中過傳統(tǒng)的生活,但忽然間,她成了納粹戰(zhàn)犯的妻子,而且她跟丈夫從一開始就聚少離多,丈夫甚至逐漸成了陌生人。門格勒夫妻的關系在大戰(zhàn)期間就已經(jīng)受到嚴重考驗,這時他們的婚姻開始解體。長久獨守空閨的伊雷妮覺得丈夫已經(jīng)變了一個人,不再是當初她嫁的那個男人。她開始尋找其他男人的慰藉,這使得丈夫暴跳如雷。約瑟夫的嫉妒心理達到病態(tài)的程度,每每妻子出門回來,他都會不斷斥責,接下來夫妻會吵得翻天覆地。這幾年來,伊雷妮早已不是原來那個忠貞賢淑的妻子。她再也無法忍受身為逃犯的門格勒所能提供給她的生活。1948年,她又一次因為出門而被丈夫罵得死去活來,但那次出門時,她認識了未來的第二任丈夫。對方是弗萊堡一家鞋店的老板,名叫阿爾方斯·哈肯約斯(Alfons Hackenjos)。當時四歲的小羅爾夫把這個大叔叔視為他人生中**個父親的角色。
門格勒知道他的名字被列在即將于1946年12月展開的“醫(yī)生審判”名單中時,開始意識到危險逼近。“醫(yī)生審判”是紐倫堡大審判中繼戰(zhàn)犯審理后的第二階段審判。先前已經(jīng)開始降低警戒的門格勒這時認為離開歐洲的時間到了。他決定遠赴拉丁美洲,于是在意大利熱那亞港登上“北方國王”號。這時約瑟夫·門格勒又有了新名字:“赫穆特·葛雷戈爾”(Helmut Gregor)。他心里還抱著希望,認為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安頓下來以后,妻兒就會立刻前去跟他會合,但情況完全不是如此。伊雷妮太眷戀德國和德國文化,完全不想離開她的家人,到地球彼端過逃犯生活。尤其是這時她的生命中已經(jīng)有了另外一個男人,盡管她對小兒子的父親仍然懷有感情,但她并不想把新的戀情犧牲掉。
伊雷妮厭倦了既有的夫妻關系,再次墜入情網(wǎng)。1954年,她提出離婚要求。羅爾夫認為母親的決定跟父親在奧斯維辛的業(yè)務活動完全無關。在這對從佳偶轉變成怨偶的夫妻之間,“什么也不問,什么都不說”曾經(jīng)是他們維系關系的相處之道。但現(xiàn)在伊雷妮很高興脫離門格勒家族,而且她特別高興自己不必跟他們要一分錢就能離開。同一年,約瑟夫·門格勒決定放棄他的化名“赫穆特·葛雷戈爾”,重新使用原來的身份。他通知聯(lián)邦德國大使館,赫穆特·葛雷格爾其實就是約瑟夫·門格勒。因此,1954年3月25日夫妻兩人正式離婚時,他用的是自己的真名。門格勒又成為門格勒,那個罪大惡極的“死亡天使”。
1956年,門格勒返回歐洲,跟家人前往瑞士山區(qū)度假,這時他終于跟已經(jīng)十二歲的兒子羅爾夫團聚。不過對小羅爾夫而言,他仍然是“拉丁美洲來的弗里茨伯伯”。一起度假的還包括約瑟夫的漂亮弟媳瑪塔(他已故弟弟的妻子)和她的兒子卡爾海恩茨。每天早上,羅爾夫都會跟他的堂弟一起爬上“弗里茨伯伯”的床,聽他說發(fā)生在蘇聯(lián)前線的精彩故事。小羅爾夫被當成大男孩看待,后來他說那次度假是他一輩子*棒的假期。小男孩非常快樂,不過他跟堂弟卡爾海恩茨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明顯。“伯伯”不斷稱贊堂弟,對他關懷備至,小羅爾夫因此感到受傷。他不知道的是,其實這位“伯伯”跟他的叔母已經(jīng)有了親密關系。
兩年后的1958年,約瑟夫在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跟他的弟媳結婚,瑪塔帶著兒子卡爾海恩茨一起跟新丈夫在阿根廷生活了幾年。
門格勒毫無困難地融入胡安·庇隆(Juan Perón)統(tǒng)治時期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當時阿根廷是逃亡納粹的新樂土,直到庇隆去世為止。然后門格勒跟許多其他納粹一樣,轉往巴拉圭生活。他是獨自前往巴拉圭,因為他的第二任妻子和繼子卡爾海恩茨希望返回德國。不若謠傳所言,門格勒在巴拉圭其實只待了兩年,1962年就到了巴西。在那些年間,盡管他恢復使用原來的身份,而且冒險回了德國兩次(分別在1956年和1959年),不過他一直沒被逮捕。在那段期間,羅爾夫的母親決定向兒子解釋父親為什么不在家,她說他已經(jīng)在蘇聯(lián)前線死亡或失蹤,不過他是個英雄。將近十年間,羅爾夫認為父親已經(jīng)死去,同時跟住在拉丁美洲的“弗里茨伯伯”經(jīng)常通信,完全不知道那個假伯伯其實就是他的真爸爸。
十六歲時,也就是在瑞士山區(qū)度假之后三年,羅爾夫終于知道“弗里茨伯伯”是他的父親——約瑟夫·門格勒。羅爾夫回憶道:“(對我而言)我父親一直是死在東歐前線的那個戰(zhàn)爭英雄,他受過良好教育,會說希臘文和拉丁文。得知真相對我造成極大的沖擊。身為約瑟夫·門格勒的兒子不是一件好事。”學校同學開始激他:“原來你就是門格勒的兒子,你爸是個戰(zhàn)犯。”他們把他叫作“小納粹”或“黨衛(wèi)軍隊員門格勒”。面對同學的侮辱,羅爾夫反唇相譏:“沒錯,我還有個叔叔叫阿道夫·艾希曼呢。”羅爾夫在校表現(xiàn)比較懶惰,他的老師們認為背后原因應該是父親不在所導致的心理創(chuàng)傷,而這個缺席的父親原本被視為英雄,后來卻成了劊子手。
雖然門格勒主動設法拉近他跟兒子的關系,但他一直無法成功在父子間建立親密的聯(lián)系。而且門格勒寫信時,筆調(diào)顯得冰冷而疏遠。他似乎復制了他跟自己父親之間的關系。門格勒為兒子撰寫了一本圖文并茂的童書,但這并無法改善兩人間的關系。羅爾夫對父親感到*不滿意的部分是他對堂弟卡爾海恩茨的關愛和贊賞。門格勒跟他這個侄兒比跟自己的兒子親近得多,他們之間的關系宛如真正的父子。對羅爾夫而言,約瑟夫·門格勒一直是個陌生人。這也正是為什么羅爾夫會需要*后那場會面,盡管那個過著隱居生活、罹患抑郁癥而且有自殺傾向的老人,那個名叫約瑟夫·門格勒的爸爸,早已不是母親從前為兒子打造的那個戰(zhàn)爭英雄。
門格勒在圣保羅的住處極其簡陋;他把床讓給兒子羅爾夫,自己則在地板上擺了一個床墊湊合著睡。無論如何,他們到了夜里仍然一直在說話,因為羅爾夫渴望為他的種種疑惑找到答案。他一開始避免提到父親參與奧斯維辛殘酷暴行的事,不過后來還是把話題帶到這個部分。父親立刻全身緊繃:“你怎么可能相信我會做出那種事?難道你看不出那些都是謊言,都是洗腦?……”老人激烈地為自己辯護:“奧斯維辛不是我發(fā)明的東西,我個人對那里面發(fā)生的事不必負責。奧斯維辛在我去以前就已經(jīng)存在了。我想幫助他們,但我的能力有限。我不可能幫助所有人。”
羅爾夫問父親火車開到奧斯維辛后,乘客立刻被篩選的事。門格勒承認他參與過那件事:“那些人到的時候已經(jīng)渾身是病,奄奄一息,我又能怎么辦?當時那邊的情況不是現(xiàn)在的人能夠想象的。”從他的口氣聽起來,他的角色“只不過是”決定誰有能力工作,誰沒有。他認為自己盡了一切可能將新到者歸入身強體健一族,因此他相信他幫助了成千上萬的人。下令滅絕那些人的并不是他,他不必為那件事負責。他發(fā)誓他從不曾親手殺害或傷害任何一個人。
對他的兒子羅爾夫而言,“身在奧斯維辛,但卻沒有每天設法離開那里,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沒有盡一切可能離開,這種行為既恐怖又令人無法置信。我永遠無法明白為什么人類會做出那種事,就算那是我的父親也一樣。對我而言,過去發(fā)生那些事違反所有倫理、所有道德,令人完全無法理解人性”。在父子兩人的夜間對談中,羅爾夫逐漸下了這個結論:他的父親對過去毫無悔意,他依舊忠于納粹理想,并且持續(xù)相信雅利安人種的優(yōu)越性。為了合理化他的種族優(yōu)越理論,門格勒提出各種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論點。如同羅爾夫所強調(diào)的,那些論點缺乏科學依據(jù),盡管父親受的是科學訓練。門格勒*后還是宣稱,他只是在盡自己的職責,為了能夠生存,他不得不遵守命令。他似乎認為這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為他免除任何罪惡感。但在他的兒子眼中,父親只是死也不肯認為自己是世人心目中的那個禽獸。
*后羅爾夫又問他,如果他那么確定自己的行為公正合理,為什么他不向當局自首,面對世人的審判。門格勒只給了這個簡短的答案:“世界上沒有公理,只有一堆急于報復的人。”
羅爾夫自始至終無法在這個人身上感受到一絲人性、悲憫或懊悔的成分。兩星期后,他離開父親時,他知道那是他*后一次跟他見面。至于門格勒,在那次會面以后,他相信他終于能安心地走了。仿佛在他告別人生以前,他覺得有必要向他唯一的后代進行自我合理化,使他不會被這個獨生子視為惡魔,而只是個單純聽從命令的人。
羅爾夫終其一生拒絕提供任何可能導致他的父親被逮捕的訊息。他說他不可能背叛父親。尼克拉斯·法郎克表示他恨自己的父親漢斯·法郎克,但相較于此,羅爾夫認為他根本不夠在意父親這個人,因此也沒有仇恨可言。
那次會面之后兩年,1979年,門格勒在巴西的一些朋友寄了一封信給羅爾夫:“我們的好友在一處熱帶海灘上離開了我們。”經(jīng)過三十四年的逃亡生涯,約瑟夫·門格勒在海邊游泳時死于心臟病突發(fā)。門格勒家族選擇對此事保持緘默,認為這樣可以避免為那些年來秘密協(xié)助門格勒的事負責。
父親死后不久,羅爾夫前往巴西整理他的遺物,并取回他的個人物品。這次旅行時,他用了自己的真正身份。他回到先前曾經(jīng)用化名住過的一間旅館,辦理入住手續(xù)時,前臺人員驚叫道:“門格勒!……你知道嗎?你的姓在我們這邊有名得很。”羅爾夫嚇得不知所措,他趕緊沖進房間,將父親的私人物品藏在天花板夾層中,盡管他很清楚萬一出事,警方不出兩分鐘就能搜到那個地方。這個“遺產(chǎn)”包括一塊金表、一些信件以及一些日記。不過并沒有任何人前來搜查,而那些日記就是2011年在那場引發(fā)一片喧囂的拍賣會中售出的手稿。
羅爾夫嚴密觀察旅館的人員進出,他設法盡可能保持低調(diào),不希望任何人注意到他,特別是那個可能向警方通報的前臺人員。就算門格勒已死,門格勒家族的秘密依然必須嚴加保守。羅爾夫·門格勒為這件事提出解釋,他說,對父親的死亡保持緘默一方面是為了保護那些幫助過他的人,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無法帶回父親死亡的確實證據(jù)。
又過了四年,門格勒死亡的消息終于廣泛流傳開來。雖然門格勒的親友和支持者早已知道這件事,但至此以前消息一直未被泄漏出去。1985年,警方終于前往門格勒的親信之一——漢斯·賽德爾梅耶家進行搜查,結果發(fā)現(xiàn)他跟門格勒之間的大量通信,以及門格勒的巴西朋友們寄來的吊唁信。
家族企業(yè)負責人、約瑟夫·門格勒的侄子迪特爾·門格勒(Dieter Mengele)這時終于不得不解除與伯伯去世有關的機密,接受媒體的采訪。對門格勒家族而言,現(xiàn)在*重要的工作是設法避免家族在門格勒逃亡期間協(xié)助他的事實對公司造成財務上的惡果。迪特爾·門格勒毫不遲疑地否認曾對約瑟夫提供任何金援,也否認跟伯伯通過信。羅爾夫被排除在那次調(diào)查外,后來他因此對堂弟感到不滿。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證明門格勒確實已經(jīng)死亡:為此,警方必須將尸體挖出來查證。羅爾夫是唯一能證明尸體確實是父親的人,但這件事進行時,他正在度假,沒有人能聯(lián)絡上他。他是在回國以后通過電視,才知道父親死亡的消息已經(jīng)公之于世。
約瑟夫·門格勒逃亡在拉丁美洲的三十年期間,有各式各樣的傳言指出他的下落,特別是以色列情報及特殊使命局“摩薩德”(Mossad)曾經(jīng)表示他們“已經(jīng)陸續(xù)發(fā)現(xiàn)他的蹤跡,只是還無法確實逮到他”。不過,雖然門格勒發(fā)瘋似地恐懼摩薩德或納粹獵捕機構的人會逮捕他,他依然大膽返回歐洲,而且重新使用真實身份。他死后被人用“沃爾夫岡·杰拉爾德”(Wolfgang Gerhard)這個化名埋葬在圣保羅附近的恩布(Embu),1985年6月6日,巴西警方在德國當局請求下挖出他的遺體。雖然透過腭骨檢查,他的身份基本上被識別了出來,但還要等到1992年的一次DNA鑒定,遺體身份才獲得絕對的證實。在那以前,羅爾夫·門格勒一直拒絕提供血液檢體供警方作基因分析。
我們難以理解,在許多國際組織和納粹獵捕者試圖擒拿他的情況下,門格勒何以能在超過三十四年期間逃過追捕。1960年,摩薩德同時發(fā)現(xiàn)門格勒以及*終解決方案主要統(tǒng)籌人艾希曼的蹤跡,但摩薩德*后選擇逮捕的是艾希曼而不是門格勒。這件事可以說明奧斯維辛的殺人醫(yī)生再度成功逃過當局緝查。但在那以前及在那之后,情況到底又是如何?
1985年,羅爾夫同意對媒體透露他跟父親會面的事,以及父親的文稿。自此,他跟家族其他成員的關系完全被切斷。
跟其他納粹的小孩相反,羅爾夫不認為有什么“殘酷基因”會遺傳給后代。仿佛為了替那個過去正式畫下句點,他決定更換姓氏,以求兒女免于麻煩。1980年代期間,他改用妻子的姓氏,并在慕尼黑成為律師,就此安身立命。
他認為他的三個孩子有權利平平安安長大,無需為祖父造的罪孽負責。他有義務讓他們知道真相,同時為他們的人生解除那個沉重的負擔。對他而言,這個家庭背景帶來的唯一好處是迫使他們思考人生本質,以及善與惡之間的沖突。他命中注定成為約瑟夫·門格勒的兒子,并因此承受種種困擾。他無法投身政治,也無法真正知道某些人——猶太商人、戰(zhàn)爭被害者——不愿與他合作的理由。2008年,在一份以色列日報上,他呼吁猶太人不要對他懷恨在心。他提到他可能會親自前往以色列,特別是去參觀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不過他也說:“可是我擔心,如果大屠殺幸存者和他們的后代知道我的身份,他們可能會感到不安。”
在本書所述及的納粹后代中,羅爾夫·門格勒是唯一一個在長年間不知道父親身份的人,但后來他卻又能針對父親在納粹死亡機器中扮演的角色與他本人進行對話。那場父子面對面的對話無疾而終,因為約瑟夫·門格勒依然相信他的理想,他認為自己并非策動仇恨的人,他甚至聲稱自己可能挽救了許多人的性命。盡管如此,羅爾夫一直無法也不愿背叛他,就算在他死后也如此。同時,為了子孫的福祉,他希望跟“門格勒”這個姓氏永遠保持距離。
豈止是德國的故事?
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基督教民主聯(lián)盟(CDU)正在柏林召開大會,忽然間,一個低沉聲響通過麥克風的放大作用,回蕩在整個會場。那是一個手掌拍打在臉頰上的聲音。
一只女性的玉手剛剛猛力摑向一名男子的臉龐,男子跟許多德國人一樣,以為可以絕口不提自己過去跟納粹的牽連。但該名男子貴為聯(lián)邦德國總理,名叫庫爾特·格奧爾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而那個巴掌儼然是在將他的過往朝他那張臉摔去。德國民眾似乎沒有質疑那個過去,因為他們終究通過投票,將他選為內(nèi)閣首長。這是1968年11月的事,在德國,僵化的道德觀與跟納粹那段歷史有關的種種禁忌都在迅速消散。與此同時,繼1968年5月的社會運動在歐洲各地發(fā)酵,德國極左翼恐怖主義團體“紅軍旅”也應運而生。
1940年代末期,大多數(shù)聯(lián)邦德國民眾盼望拋掉過去,展開新局,并終止進行中的除納粹化行動,因為許多人認為那是同盟國強迫實行的措施,結果反而有礙德國的民主化。德國總理急于取得民心,為了表示愿意傾聽人民的聲音,他結束除納粹化運動,并展開平反一部分納粹黨人的程序,僅將罪證確鑿的戰(zhàn)犯完全排除在外。這項政策嚴重妨礙了控訴及逮捕許多前納粹要員的工作。戰(zhàn)后約瑟夫·門格勒一度在德國逍遙法外,就是一個完美的實例,但逃過司法制裁的絕不只有門格勒一個人。
打了總理耳光的人是一位名叫碧雅特·克拉斯費爾德的年輕德國女子,她下定決心要勇敢面對父母輩在納粹時代的那段過往。先前她已經(jīng)到德國國會大樓前高喊“基辛格!納粹!辭職!”這次她則公開賞了那位“納粹老爸”一記巴掌。在當時的德國,世代沖突因為國家社會主義的歷史重擔而更形惡化。阿登納擔任總理的時期被年輕德國人當成抨擊的箭靶,1968年的學運青年奮起反抗現(xiàn)狀,他們拒絕接受前納粹黨員在聯(lián)邦政府中擔任要職的情況。
充滿象征意涵的打耳光畫面永遠烙印在德國人心中,而所有曾經(jīng)以為能夠向家人及世人掩飾自己過去的人都因此而坐立難安。1950年代出生的德國人是**個不曾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的世代,他們完全不怕仔細檢視那段歷史。他們再也不可能滿足于“希特勒必須負全責”這種推卸責任的陳詞濫調(diào)。
賞總理耳光是碧雅特·克拉斯費爾德交付給自己的任務。那時她跟知名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走得很近,這位作家厭恨基辛格,一如他在更早以前憎惡阿登納。格拉斯是戰(zhàn)后德國的“道德良知”,1959年出版的著作《鐵皮鼓》(Die Blechtrommel)是關于第三帝國的*權威撰述之一;他還寫過許多其他精彩作品,199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2006年,在即將迎接八十大壽之際,他卻忽然掀起波瀾。自傳型作品《剝洋蔥》(Beim Huten der Zwiebel)出版前夕,他接受德國《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egemeine Zeitung)專訪,忽然透露自己曾在1944年年僅十七歲時加入惡名昭彰的納粹武裝黨衛(wèi)軍。2006年,他接受法國《世界報》(Le Monde)采訪時表示:“這件事一直折磨著我。我在這么多年間一直保持的緘默是促使我寫出這本書的原因之一。該說的話,終究得說出來。”
1968年,也就是總理被打耳光那年,格拉斯的過去仍舊是個秘密。誰會想到這位被視為戰(zhàn)后德國思想導師的大作家曾經(jīng)是個納粹?人們怎么可能料到他會在半個世紀中完全隱藏自己進過武裝黨衛(wèi)軍的事?君特·格拉斯一輩子致力關注人民跟納粹勾結或罪惡感這類議題,仿佛這一切都在呼應他自己的人生。這名極力主張“勇于擔當,面對過去”的人士怎么可能以為時間的流逝和他對自身的反思行動足以消弭那個不可磨滅的污點?他讓緘默成為常態(tài),結果差點導致畢生奮斗被蒙上永遠的陰影。身為一名偉大的作家,格拉斯無懈可擊地體現(xiàn)了德國是如何對歷史保持緘默,以及這個國家必須面對多大的艱難阻滯,才得以打破沉默,接受令人無法接受的事。
“重建民主的前提是避談過去”,這是在戰(zhàn)后德國一度流行的理論。到了“勃蘭特年代”,這種論調(diào)終于被全面推翻。1970年12月7日,聯(lián)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在他的忠誠支持者之一——君特·格拉斯陪同下前往波蘭,代表全體德國人民在1943年華沙猶太居住區(qū)起義事件紀念碑前下跪,請求波蘭原諒納粹犯下的殘酷暴行。在那個莊嚴肅穆的時刻,勃蘭特說出這句名言:“我在做的是人類在言語無法表意時所做的事。”如同歷史學者諾伯特·弗萊(Norbert Frei)所言,必須經(jīng)過好幾個世代的時間,那段歷史以及猶太人大屠殺造成的深遠影響才能變得可以讓人承受。因為,我們確實有必要區(qū)分“知道”和“承受”這兩件事。1990年,弗萊指出新生代民眾對大戰(zhàn)沒有(或幾乎沒有)切身記憶,也不會有任何個人層面的自責心理,因此他們終于不再被迫背負政治及道德責任。
人在情感上的牽扯越多,就越難以拉出進行道德評斷所需的必要距離,仿佛承認父母犯下的暴行會無法挽回地玷污自己對父母的孝心。我們很難說出這種話:我知道我父親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同時我也愛他。若要達到這種心境,人必須走過一條艱苦漫長、布滿陷阱的路。
相反地,如果情感淡薄,就比較有評斷的余地。或許因為這個理由,那些在童年時代比較少得到父親關愛、甚至從不曾見過父親的人,他們會比較容易對父親做出道德判斷。對孫子輩或侄甥這些親屬關系稍微比較遠的人而言,要背負某種罪惡感或許也比較容易。馬蒂亞斯·戈林、卡特琳·希姆萊就是很好的例子:對他們而言,“那個魔鬼”是個他們從不曾謀面的遙遠人物。
除了情感上的親疏,還有一個因素是時間上的遠近。物換星移、歷史更迭(例如柏林圍墻倒塌),過去似乎因此變得比較能讓人接受。納粹主義予人的觀感會隨著時間而變動,就像不同年代的歷史學家對它也會作出不同的分析。時光流轉,世人對往昔那些罪惡有了更多了解,納粹的孩子們不得不承認德國的過去,并通過這面棱鏡承認自己家庭的過去,這其中摻雜著緘默心態(tài)在其跨世代面向上所隱含的一切。
在本書講述的那些納粹孩子們的人生路途中,他們都經(jīng)歷過德國面對納粹主義時所抱持的緘默態(tài)度,但在“家庭”這個層面,他們卻沒有感受到世人表現(xiàn)出相同的緘默。大戰(zhàn)結束以后,他們必須背負身為某某人子女的事實,并在清楚知道父親涉及那些泯滅人性的罪行后,默默承受那個過往。他們的家人絕口不提的并不是他們的父親當過納粹這件事,因為畢竟無視這個事實是不可能的事;那些家人只是不愿談論他們的父親在什么程度上參與了第三帝國的瘋狂屠殺行動。
這些孩子永遠無權說“爸爸不是納粹”——在此援引哈拉爾德·魏爾策(Harald Welzer)、扎比內(nèi)·默勒(Sabine Mller)及卡洛利妮·屈格納爾(Karoline Tschuggnall)聯(lián)合著作《爺爺不是納粹》的書名。大戰(zhàn)期間,他們是英雄豪杰的孩子,戰(zhàn)后他們卻成了“屠夫的小孩”。他們忽然置身于一個全新的世界秩序中,在那里變成人人唾棄的賤民,但他們未曾有任何機會提前做好心理準備。童年時代的他們不可能不知道父親跟權力中樞和希特勒之間的緊密關系。當時局證明希特勒是人類歷史上*為罪大惡極的敗類,他們明白自己因為與父親的血緣關系,被迫跟希特勒緊緊糾結在一起。此外,除了沃爾夫·呂迪格·赫斯、小阿爾貝特·施佩爾以及羅爾夫·門格勒,納粹的孩子們在紐倫堡大審判以后都不曾見過父親。因此,他們沒機會跟父親面對面攤牌,無法詢問那些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問題。就算是原本有機會這么做的人,在面臨如此沉重的試煉時,他們也經(jīng)常不禁退卻。但是,他們?nèi)急仨氈币曇粋€事實:他們是納粹的孩子。
為了自我建設,有些人選擇在心中淡化父親參與納粹恐怖暴行時的自愿程度,有些人則選擇激烈排斥,不讓親情有存在的余地。要想讓自己對父親的深沉感情與對他的殘酷行徑所感受的罪惡感同時并存,這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心理工程。然而,一旦他們的姓氏被提及,他們必然都得面對社會的反應;無論他們決定跟自己的血緣維持什么樣的關系,那個姓氏都宛如宿命,無可避免地將他們拉回那條血脈。
在德國,一直要等到科爾總理的年代,等到不曾經(jīng)歷戰(zhàn)爭的世代正式掌權,以及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墻倒塌以后國家統(tǒng)一的時代降臨,德國人才終于全面重新審視及探討那個黑暗過去。罪惡感曾經(jīng)只被加之于納粹迫害的少數(shù)主事者身上,但兩德統(tǒng)一以后,整個德國都愿意承擔那份罪惡感。
同時,完整傳承與納粹有關的記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恐怖可能通過其他形式重新出現(xiàn),近年各種新型極端主義的興起就是一個明證。希特勒永遠不會回來,但跟當年導致希特勒崛起的時勢類似的情況很可能重新上演。過去的教訓是否能成為對抗各種極端主義的堡壘?我們希望是如此。希特勒青年團的世代業(yè)已凋零殆盡,其后已經(jīng)陸續(xù)出現(xiàn)四個新世代;現(xiàn)在不再有人禁止我們設法了解在那樣的社會、經(jīng)濟及法律環(huán)境中,我們自己會采取什么行動。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親身經(jīng)歷過那個時代的劊子手和受害者已經(jīng)越來越稀少,不久以后他們就會完全退場。隨著他們的消失,當事人的主觀記憶也將灰飛煙滅。納粹政權那些頂層要員的名字必須繼續(xù)為人類的未來敲響警鐘,但為此,我們還得妥善保存關于那個時期的知識。不幸的是,現(xiàn)在的年輕人因為無知或缺乏興趣,有時似乎對歷史不屑一顧。當然,如亞歷山德拉·厄澤爾(Alexandra Oeser)所強調(diào)的,我們不可以一概而論。厄澤爾在她的著作《傳授希特勒:德國青少年面對德國的納粹歷史》中指出,世代、社會背景、性別、政治傾向乃至學業(yè)成績不同,人跟納粹主義之間的關系也會有很大的差異。
這樣的分析同樣適用于納粹的后代。無論那些父子或父女的關系是以共同生活還是書信往返的方式存在,我們都會在這些納粹小孩身上發(fā)現(xiàn)某些共同點:他們一直都知道自己的父親信仰國家社會主義,但他們都是在戰(zhàn)后通過第三方才得知自己的家庭在德意志第三帝國中所扮演的角色。歷史未能給予他們足夠機會否認父親的所作所為,盡管其中某些人竭盡所能想要相信,作出那種否認行動是可以辦到的事。在其他方面,這些納粹小孩每一個都是獨特的個體,各自以特殊而復雜的方式跟自己的家庭歷史達成某種妥協(xié)。這其中牽涉到的因素很多,例如性別(男孩或女孩)、家庭結構(單一子女或眾多兄弟姐妹)、情感聯(lián)系(母親是慈祥還是冷酷,父親是關愛還是疏遠)等。當然,某些人的人生路途有相似之處,但沒有一條路跟其他的路一模一樣。所有人之間的唯一公約數(shù)是,他們都不可能無視自己的家庭歷史,因為那是個沉重無比的負擔。許多納粹小孩甚至決定將自己的生命奉獻于此。另一方面,盡管小阿爾貝特·施佩爾在事業(yè)上飛黃騰達,但他一輩子都得為這件事傷腦筋:所有人見到他時問他的**個問題都跟他的父親阿爾貝特·施佩爾有關。
就像這些納粹小孩永遠被父親的命運糾纏,納粹的歷史在世人的集體記憶中將歷久彌新。就算有一天,世界上不再有當年的受害者可以提供見證,就算到時,捉拿*后幾名納粹罪犯的工作已經(jīng)遠去,那些名字激起的反響將持續(xù)引人深思。
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個人歷史與人類的歷史早已無法分割。
納粹的孩子們 相關資料
這本一流的圖書成功完成了這一特別艱難的主題。 ——法國《費加羅雜志》
歌德倫•希姆萊、艾妲•戈林……這些第三帝國高官的子女們的命運如何?塔妮婭•克拉斯尼昂斯基追溯了他們的命運。 ——法國《星期日報》
塔妮婭•克拉斯尼昂斯基并沒有對這些第三帝國高官的子女們的行為做出個人評判。她記錄了他們每個人的態(tài)度——明白該如何面對一段遠超出自己命運的殘酷歷史。 ——法國《觀點雜志》
納粹的孩子們 作者簡介
塔妮婭•克拉斯尼昂斯基(Tania Crasnianski),生于法國,母親是德國人,父親是法俄混血。曾為法國巴黎律師公會刑事律師,目前在德國、英國及美國生活、創(chuàng)作。《納粹的孩子們》是她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后廣受好評,已被翻譯成九種語言,譯介至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qū)。
- >
唐代進士錄
- >
詩經(jīng)-先民的歌唱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旅程
- >
經(jīng)典常談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山海經(jīng)
- >
姑媽的寶刀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